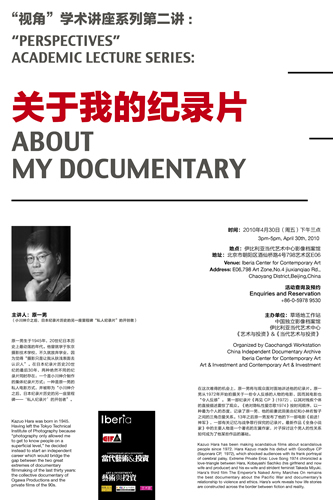
这是穿插在原一男先生回顾影展中的一场讲座,被安排在《前进!神军》放映刚结束后。原先生作为日本“私记录片”的开创者在这次放映活动中被带入国内观众的视野。他作品中的“私”,不简单地意味着拍摄者和他的生活作为影片的内容被记录,甚至不仅仅是指影片中作者“强加”的视角和“设计”的情景,原先生赋予他影片的“私性”一层更潜在的涵义。原先生的纪录片诞生于他对那些早于他的日本六十年代纪录片和纪录片工作者的思考中。像小川摄制组那样集体式的工作方式,以及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大的社会问题中寻求变革的可能性,在原先生看来是属于“上一代人”的,他感觉自己已不再能认同那种集体的观念,转而从个体和自身出发,寻找社会中权力真正存在的地方——人的内心。在这次讲座中,原先生以问答的形式谈到了他提出的虚构纪录片的概念,制作纪录片对于他的意义,以及一些影片画面外的内容…… 原一男: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问的,都可以现在说一下。我可以讲很多事情,但是不知道你们想听什么。从那个小小的日本过来的,年纪已不轻的我,你们想听什么呢?你们已经看了三个片子了。 提问:看了《前进!神军》这部影片后我非常感动,感觉那个片子里男主角奥崎的表情,包括他非常迷信的表现很关键,在整个片子的质感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导演在拍和构思的时候是不是跟他之间有一个很有效的沟通?还是本身他的个性就很强? 原一男:对奥崎来说犯罪是他自我表达的一个方式,他一见到人就说:“我其实有三个前科。”对他来说这个前科是他的“勋章”,他的想法和我们普通人是完全相反的。他每次犯罪之后就被关到监狱里,每次他都是单独的一个房间,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但就是那个时候他才会放松,在那儿他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悖论——他只能是在被关起来,没有任何自由的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每次从那儿出来,他又不自由了,又开始想,我还要干一些什么。他给自己一个压力,就是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你能理解他这个人吗? 其实这个电影也是关于我的自我探索的,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但尽管我懦弱,在我内心深处还有某种暴力的冲动。我一直对自己感到害怕,我要压抑那部分东西,要不然它会把我弄疯的。整个电影花了五年时间,但是拍摄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最后在奥崎和山田对峙的镜头里,他们两个激烈地争论,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两个都是把自己整个人生的能量和激情拿出来在那儿相互对峙,那是种最激烈的能量之间的一个较量。我当时有种冲动,不是说当时出于任何理性,就是到他们最激烈交锋的力量中心点去。一般的话两个人在对峙,我们应该在他们第三角的位置,来回摇着拍摄。那个时候我在他们俩之间,激烈对峙线的中间,我站到那个中间去了,于是我就拍了这个状态,一般不会是这个状态的。一直拍了十一分钟,那个时候一盘胶片只能拍十一分钟。在那儿我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暴力冲动发泄了,每个电影里都会有这种东西,这个电影就是在这个地方。于是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制服我内心的野兽,这样我才能活到今天。 在《绝对隐私•恋歌1974》里面也有这样的地方,就是生孩子那场戏,因为我不用投入其中了,她就是正对着我,那个孩子就生了出来,我已经是在那个接受的状态上。然后在最强烈的磁场里面,把自己内心的东西散发出来。可以说这是我拍纪录片的最大动力。其实奥崎在电影里显得好像是很强悍,很粗暴的一个人,他不是那样的。有一次他在东京开着车乱转,碰到右翼的那些人,那些人就说:“哎,靠边儿。”然后那个车就停在奥崎车的前面,上面有一个年轻人就下来走到奥崎身边,他怕那个年轻人过来打他,所以他就在兜里拽着一个扳手,那个时候他必须得把自己全身的杀气充好了电,等年轻人过来的时候就先发制人了。奥崎总谈起暴力,他知道自己不是那么强硬,其实对他最重要的不是跟一个人打架,是跟整个国家政权在打架,所以必须要有很大的能量才行,他每天想的都是我怎么才能充满这种能量,然后他想了一个招就是积攒愤怒,理解吗?他利用摄像机,在这个电影里积攒他的能量。我们都是这样,被拍摄的时候是比平时更有能量的,更注意力集中,所以他其实喜欢被拍摄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要利用摄像机的在场攒够了能量,真的去杀影片中那个中队长。经常有一些观众跟我说:“也许你不拍他的纪录片,他就不会去杀那个中队长,让中队长受重伤。”我也同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拍纪录片是一个可怕的,危险的行为,但是奥崎渴望这种危险。 纪录片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这个电影里,奥崎认为自己是“神军平等兵”,平时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态度特别谦恭有理,客人是很多的。一说要拍摄了,他就开始变成“神军平等兵”了。这个“神军平等兵”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的,奥崎的想法是日本的天皇制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他觉得应该否定这个国家,建立神的国土,这个神的国土才是自由的,没有限制的,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他要为了实现这个而去斗争。在摄像机面前,奥崎在表演变成一个神军平等兵,在电影里他是作为神军平等兵来活着,电影中有两个他自己,一个是平常的自己,一个是电影中的自己。神军平等兵是他理想的自我形象,他在摄像机前表演他的理想形象。如果说从推理上来说,他就是想在电影里面表演,来实现他理想的自我性,以此做一种自我完成。他有一次对我说:“能够表演奥崎谦三的,只有我奥崎谦三本人。”当然了,谁能演他呢?你能感觉到吧,他先看了,我那边是不是准备好开始拍了,才开始正式地说话。我特别讨厌他每次都是这样,然后我就想他的演技很糟糕,他其实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想实现自我解放或是自我完成,其实从电影语言上来看,这就是虚构。所以我的这些纪录片,最基本的东西是“虚构”。《恋歌》里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生孩子的那个镜头,前边都是为这个镜头做铺垫的。对美由纪本人来说,她不想向她的母亲一样被制度和社会束缚着,她要通过自主生孩子来从那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其实是这样的,她来演出一个女人如何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完成了成为新的她自己。 日本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电影杂志,叫《旬报》,非常有名,每年都要评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后武田得了最佳女演员奖。然后还有很多批评家来、选奥崎为最佳男主角的候选人,武田得的是第二位女演员,奥崎也是第二,这个听起来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纪录片的人物跟剧情片不一样。纪录片和虚构电影、剧情片之间的疆界已经取消了。我不是说所有的纪录片都是这样的,我指的是我自己的这一类纪录片。我认为十个导演有十种电影方法和理论,对我来说纪录片是这样的。我的这种电影方法是在七十年代,自己考虑和实践出来的。说得太长了,你们有什么想提问的吗?我刚才回答那个电影,现在讲演怎么办呢?已经走到这儿了就这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