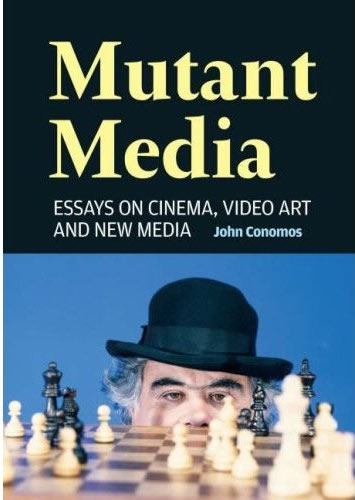 电影(Cinema)、视频艺术(Video Art)以及新媒体(New Media),当我们提及这些概念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反应是,显而易见,我们所意味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电影属于大众文化范畴,视频艺术和新媒体则属于当代艺术;电影被认为是保守的,样式化的,视频艺术和新媒体则被认为是实验的,保有先锋性的;对于电影的理解和讨论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框架下的,而对于视频艺术和新媒体的讨论则被认为是属于艺术史,特别是当代艺术史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上述所言是一个既定的观念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提这样一些问题:电影属于当代艺术吗?电影可以属于当代艺术吗?什么样的电影才可以属于当代艺术?同样属于影像媒介,电影、视频艺术与新媒体之间的边界究竟如何划分?这同样也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批评家及作家约翰•克纳莫斯在《突变的媒介:关于电影、视频艺术以及新媒体》一书中所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凭着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电影的兴趣,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视频艺术以及新媒体艺术的关注和亲身参与,运用文化批评以及影像批评理论,约翰•克纳莫斯在这本书中,从一个不同以往的研究角度,对于各种影像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定位。 电影终结了吗? 克纳莫斯曾经对法国的电影理论家和批评家雷蒙德•贝鲁尔(Raymond Bellour)的理论思想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克纳莫斯在这本著作中,明确地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以影像为基础的视频艺术和新媒介的出现并非是对于传统电影观念的挑战,反而应该被视为电影这一传统媒介得以延续的证据。视频艺术和新媒介对于电影的这种延续性,与电影历史上任何一次的电影形式和电影观念的更新发展都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他们的出现可以被理解为电影史上的又一次由技术和观念所推进的电影媒介的突变(Mutant)和更新。 克纳莫斯列举了电影史上诸如布努艾尔(Luis Buñuel)、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杰弗里•肖恩(Jeffrey Shaw)等一系列给电影形式和理念带来革命性创新的电影艺术家,试图通过对于电影革命性与电影延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界定,以此来理解今天的视频艺术以及新媒体艺术。在这样的预设前提下,在人们观念的中本应属于当代艺术系统的视频艺术和新媒体艺术重新被放置于电影史的发展逻辑之中。 在克纳莫斯看来,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是政治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指涉的,更是一种具有实验性的媒介。而视频艺术或是新媒体艺术只不过是电影对于新技术和新文化的出现的一种反应形式,是突破了传统电影媒介边界的突变体。 走向更新的方法论 克纳莫斯与他的前辈法国的电影导演戈达尔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拒绝承认对于电影而言,存在所谓“辩证的(Dialectical)”边界。与大多数的新媒体批评家和理论家不同,克纳莫斯对那些有悖于传统电影观念的所谓“新影像理论”毫无兴趣,反而认为传统的电影形式和观念依然作为理解这些新影像媒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发挥作用。 今天的当代艺术,无论在创作环节,还是在阐释环节,都异常地排斥通过技术性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来对其进行划分和界定。推动当代艺术发展和提升的是批评性和抽象性的概念所组成的框架范式。将艺术视为文本来进行编码和阅读被认为是当今有效的创作和写作形式,但在克纳莫斯看来却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影像运行的真正动力来自于观念与实践这对矛盾之间的张力,而非概念之间的抽象推衍。 克纳莫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将电影、视频艺术以及新媒体艺术视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来考察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通过与不断更新的技术和文化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联,来重新思考和界定各种影像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电影并非是一种单一固定的影像形式,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相互纠缠指涉的多样形式的混合体。 一个文化地理学样本 克纳莫斯本人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具有希腊血统的澳大利亚人,是电影制作者、视频艺术家、诗人、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作家,同时,又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艺术学院的艺术学教授,主要讲授电影研究以及新媒体研究等课程。 因为这样的身份背景,克纳莫斯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也投向了澳大利亚的影像艺术。他通过自己的亲身创作经历以及相关的展览活动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说明和讨论。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讲,澳大利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经济发展程度上,它都处于北美洲和亚洲之间。但是,与此同时,令人感到尴尬的是,澳大利亚仿佛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又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它的位置仿佛永远都是“之间”。这也造成了一种情景,那就是,在面对文化交流时,澳大利亚好像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文化进口的位置。尽管澳大利亚的部分学者认为,这样的“之间”位置反倒有利于澳大利亚对于不同地理文化形式的吸收和融合,但是,他们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本国自发的主体性文化形态也会随之减弱和消失,而所谓的文化融合却是要以本国家本民族的原创性主体文化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样的文化情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影像艺术的观念和形态呢?这也是克纳莫斯试图在书中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