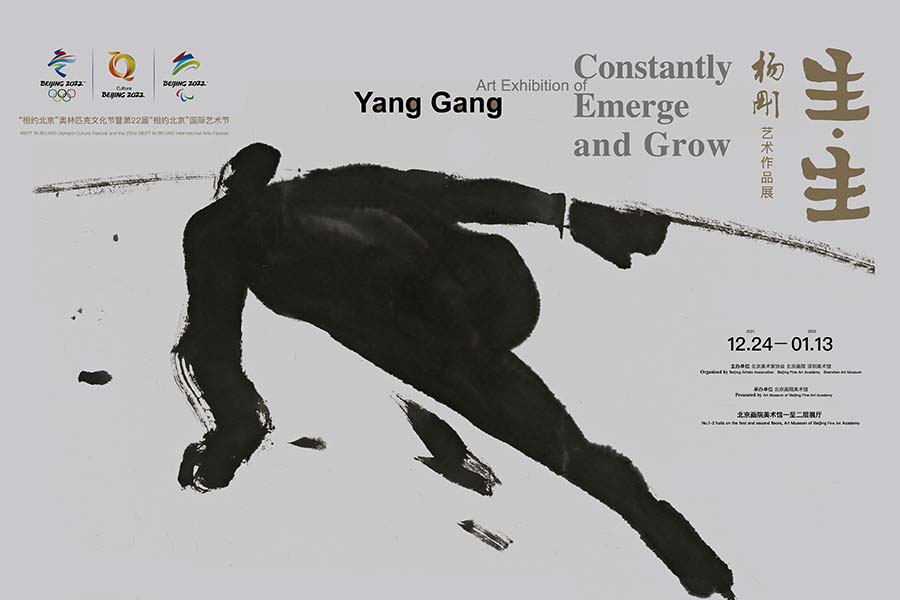周宪将“意义”问题归结为“范式”问题,认为艺术意义经由了由古典朴素实在论范式、现代自律论范式到后现代对话性和多元论意义范式的演变,而这一过程又是能指/所指、文本/实在、艺术符号/其他符号、日常经验/知识间不断由统一、分离、对抗的过程,这一历史嬗变不仅是艺术表达意义方式的变化过程,也是公众理解文本意义方式的变化和批评家对文本意义注解方式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意义便被视为一种生成的多元过程,它实际上有赖于一种艺术家 —文本—观众之间复杂的互动与对话。意义的探寻与其说是一种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对话过程”{周宪:《意义及其范式》,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4 期。}。
高世名则侧重分析了邱志杰的“文本含意缺失”这类形式原理所导致的危机和危害。他指出,从接受的角度看,“含意缺失的艺术文本”在文化境况中并不能逃脱外在释义的侵扰,反而会因其不确定性而导致作品实现过程中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以作品的“主观解读模式”和“本文游戏模式”为基础,前者以读者代替作者,“仍是将艺术文本预设为含义载体,只是取消了原典意义的合法性,而以个人经验的合法性取而代之,它正是批判形式主义的内敌”; 而后者“将艺术文本看成不受语言结构所限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游戏场所,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迷狂”。他认为,多元论所宣称的无限可能性是一种无法成立的 “幻象”,因为“文本的产生与接受皆赖于我们文明中的历史沉积(我们正是依据它们去思考、创造),而这些沉淀恰好来自语言的实践与应用。……艺术文本的作用与生效也都是在语言结构之内实现的,是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职能”。他还指出多元论在文本接受中的两种基本模式反映在创作中则呈现为“极端封闭的私人经验”与“极端开放的零度创作”,前者“往往仅存在于生理与私人经历的水平上,缺乏对历史文化维度的关涉能力以及对日常语言结构的批判性功能”,而后者“是非意图性的无指向的纯粹形式操作。它与语言的社会性功能根本对立,而将艺术设定为一种沾沾自喜的语言游戏”。他最后指出多元论及两种接受和创作模式的危害,从语言学角度而言:“无限可能的多元实际上呈现为一元状态,且是毫无可能性的一元,无限延迟的一元。”从文化学角度而言,它又可能使我们的当代艺术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陷阱,丧失自省意识和怀疑精神。{高世名:《无限可能性的不可能性》,载《江苏画刊》1995年第11期。}
王林认为邱志杰以语言学方式谈论艺术意义的先在错误是没有意识到“艺术和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并不等同”,“把艺术创作等同于语言研究更是一种理论误读与误导”。他指出,“语言”与“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系统化和强制性的,是人类理性化的交际工具,没有个人创造的余地;而艺术则是非系统化的、非强制性的,从本质上讲是感觉化的交际工具和一种个人生存方式及人与人联系的方式,人类精神世界的自足性决定了艺术不可能符号化,相反它是“反符号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是对语言的抵抗,是对符号世界的既成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抵抗。反过来,艺术之所以是直觉的情感活动,就是因为只有在直觉和情感之中,人对事物的感知才可能是真正个人的、原初的和直接的”。从这种“艺术直觉表现论”观点出发,他指出“艺术是‘语言’和言语合一的人类活动,或者说它只有言语没有语言,不能为理性所穿透……我们只能在关于言语,在关于言语和语言关系的讨论中去汲取对艺术研究有益的东西”。他同时指出艺术作为言语话动,不可能是无意义的,不过“所指意义是由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与具有确定规则和具体内容的日常语言的交际方式不同,它是以物质材料形式呈现,并具有非系统性的行为方式”,是主体间的“交际碰撞”,“意谓传达主体生产意义,接受主体也生产意义,而文本不过是发生碰撞的场所”,艺术信息甚至具有某种神秘的特征:“包含着非语义的宇宙体悟和超语言的生命智慧”,他的结论是:“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主体的输出,而是主体间的碰撞和主体自身的建构。”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还积极估价了批评在创作和接受文本时的作用和局限,一方面批评指出了文本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它只能通过对艺术的有限的符号性研究来认识艺术反符号的性质,因而任何“夸大或无视符号性都会误入歧途”。应该说,王林强调艺术与语言在交际传达方式上的差异,强调语言和言语、共同性和历时性、形式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关系对于纠正“批判形式主义”混淆语言与艺术界线,片面强调形式语言的共时性特征的偏颇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将这种差异夸张到对立甚至对抗的程度,这无形中又削弱了他所强调的艺术的社会职能,尤其是将艺术仅仅视为主观直觉性的体悟活动更使其理论难以具有“超越索绪尔”的能力。{王林:《超越索绪尔》,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3期;《本体论的终结》,载《江苏画刊》1995年第8期。}
马钦忠正是从王林在使用语言学概念的矛盾和错误中试图清理出问题的症结,他指出王林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分清从语言学的语言到艺术学的语言中的三个问题,即其一,词义的静态义,他当成言语,而事实上它恰好是语言在抽象后的“一般”;其二,把艺术学作为方法论应用的“语言”和“言语”等同于人们交流的现实基础的“话语”;其三,在模糊了中间环节之后,又站在艺术活动的“一次性”上返回到Linguistics Theory的“语言”中舞枪弄棍。他认为这场有关意义的讨论在语言学层面的展开如果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理论进行“即兴演讲”是很危险的,他主张“把艺术作品看成一种语言行为,实质上是放在社会交流这一层面来剖析它”,应该将文化学、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还原为社会功能这一艺术的基本问题。他认为,艺术语言有四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从社会交流形式上不应将“艺术语言”与“言语”对立起来,“艺术语言就是指艺术作品在社会之中的交流方式”;其二,作为现实化的物质存在的作品是一种“公开性”和“公共性”的事物,“艺术发展史是一个不断由个人语言创新到转化为‘公共性’的历程”;其三,是指艺术家把材料和技法结合起来进行内在主观情思的“公共化”的问题,即独特的内在意识状态、情感体验一旦转化成为物质存在时便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公共性”状态;其四,材料转化成艺术语言也必须借用材料的“公共性”语言,如装置和行为艺术。{马钦忠:《怎样超越索绪尔》,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12期。}
如果说,在使用语言学方式讨论艺术意义的问题中,邱志杰沿用的是索绪尔及结构主义的传统并由此滑向对结构主义反叛的极左方面——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的话,那么,上述讨论者则似乎是在巴赫金所代表的俄国语言学传统的方向上展开着对结构主义形式论的批判,巴赫金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修正和批判类似于历史哲学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巴赫金将语言和言语这对在索绪尔那里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强调言语是在“言读”和互文性中,即在具体的历时性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它既不同于反映论的再现,也不同于结构论的网络,这样,他就将形式主义共时性的语言问题与深广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维度联系起来,正确地指出了语言意义的来源并不存在于符号和网络的共时性差异而来源于历时性语境和社会身份的差异。应当说,在有关当代艺术意义的讨论中,强调意义问题与历史—社会—政治等情境的关系,以及强调这种关系所反映的社会职能和批判性质表明了这种讨论的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趋向。
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他们希望有关艺术意义的讨论从语言学方式重新回到艺术实践批评这一问题起点上来,而不要沦为纯粹学理性质的论战。顾丞峰指出产生这场讨论的“实践背景”是近年来国内大量非架上的装置、行为艺术的出现使我们所熟悉的批评和阅读工具“失去针对性和效力”,对这些作品的理论定位和认定成为这场讨论的急迫性所在,因此他认为“纯粹的理论阐释十分必要,但结合分析具体作品可能更有说服力”,秉此原则,他将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分为“艺术状态”和“状态艺术”,前者指1989年以后以个人生存状况为创作出发点的创作方式(如“玩世现实主义”作品),后者指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指向隐晦、意义不确定的装置、行为艺术作品。他侧重对这种 “意义的模糊”的创作进行了理论背景的分析,认为“模糊并不是空无,它具有多义性,多义性为不同的读解者留下更多观照的空间”,它源于西方现代理论中解构主义的思维框架,他认为邱志杰所代表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有“试图弥补完全解构可能带来的虚空的一面”,它在运用解构主义方略的同时也开始植入批判的标识,融入了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顾丞峰:《从艺术状态到状态艺术》,载《江苏画刊》1995年第8期。}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