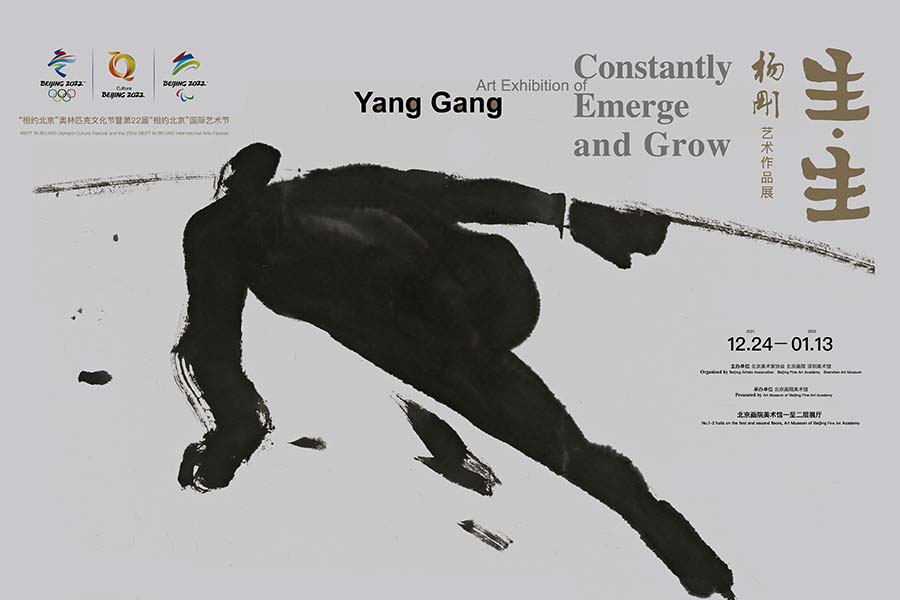邱志杰以语言学方法介入到这场讨论,并形成与易英谈论艺术“意义”截然不同的理论方式。邱从索绪尔语言学中“差异系统”的基本原理出发,首先将语言分为“日常语言”和“艺术语言”两种对立的系统,前者指有明确所指的能指,“符号的意义来自能指与所指的精确对应”;而后者则是“语言系统的自生产活动的产物……它是无所指的或曰有无穷所指的”(后来,他又对这一对概念做出修正:日常语言是有“指涉物”的;而艺术语言是没有指涉物但有“所指”),“艺术话语唯有自我指涉,保留一种结构感,抗拒自身中潜伏的麻醉力才可能提示世界的结构感”,他将这种“纯粹能指”的形式主义艺术观称之为“批判形式主义”,以区别于“诉诸视觉愉悦”的“古典形式主义”和“以表现论为模式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这种艺术观将艺术现实主义的传达功能转变为认识功能:“艺术是对生活的语言性的认识活动,是以语言的自我指涉行为不断对语言麻醉力的消毒,为存在的真实与自由感划定界限。”所以,“正因为艺术是无所表达的,没有意义的,它才是有价值的”,艺术史就是艺术话语被某种释义附着,出现所谓“所指固化”,艺术语言被日常语言消化吸收,而语言的能指网继续生产新的“纯粹能指”这样一个无穷反复的“纯艺术的形式主义发展史”{邱志杰:《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载《江苏画刊》1994年第12期。},从这种逻辑出发,他主张用“有效性”和“生效”这类概念代替“意义”这个概念:“一件艺术品虽然是没有含意的却仍然是有价值的,唯其是没有含意的,它才真正是生效的。”他还对艺术的这种 “有效性”和“自生产能力”进行了考察和阐释,认为“有效性”不是某些独立因素单值作用的结果,而是艺术的各种“形态”元素(介质)整体活动的产物,他认为艺术的“自生产能力”来源于 “符号的任意性”这一基本原则,这类自律理论类似于有机物生长中的“整体论”,它强调基因内存在的“生命力”大于环境因素的干扰:“艺术形态不但会在环境中变化,而且直接促成环境的变化。艺术品不是环境变化的被动反映者和反应者,而是其积极促动因素,并且是环境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他还主张用“情境” 这一概念代替“环境”这一概念,以消除迷信“环境”的各种庸俗社会学,情境不但不同于环境,“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对环境的概念”,艺术的“动源”和自动能力与“情境”的关系是互动性的而不是反映性的。{邱志杰:《反思与追问》,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8期。}
从这样的形式主义艺术观出发,邱志杰选择了三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形态作为他的批判对象:客观表达对象的艺术、主观表达直觉情绪等内在体验的艺术及表达各种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的功利主义艺术,他尤其针对第三种艺术展开批评,“因为如果它服务于任何一种思想它将降格为诸多思想之一而失去对一切思想的麻醉力的防范监督功能从而根本丧失其批判性”,而“艺术正是对灵魂的惰性持久的追问。而只有在自我更新中保持其形式主义的纯粹性才可能持续与非艺术的日常语言对立,从而保有其自身的批判品格”{邱志杰:《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载《江苏画刊》1994年第12期。}。在《一个全盘错误的建构》一文中他指出易英谈论艺术“意义”的错误不仅在于他混淆了“意义”和“含意”的界线,而且在于他只谈“含意的传达”而对艺术的“真正生效方式”置之不理,“含意的传递既不是日常语言的唯一任务,更不是艺术话语的先天任务。含意的缺席并不是价值的空无,相反,在艺术中恰是这种含意的缺席是其语言生效的必要条件”。“力求明确的意义”这种“意义”理论是建立在传统现实主义表达理论基础之上的,它将艺术语言等同于日常语言,“要求艺术家改用大白话直陈而免除转译的困难”,而这种“文化意义”的转达理论只能将“艺术”降低为“年画、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画”。他还对易英的“二次裂变”提出质疑,认为它反映了一种“历史宿命论的信念”和“改朝换代的错觉心态”。总之,他认为易文的观点是“企图用政治取代哲学,用技术取代科学,用符号的含意取代艺术的感觉而否认艺术的实验状态;它在把艺术由语言的调整推向意识形态的干预时也把艺术由超越的路径变成了现世的工具……”{邱志杰:《一个全盘错误的建构》,载《江苏画刊》1995年第7期。}
如果说,在论述“批判形式主义”时邱志杰还是一个索绪尔式的语言中心论者,那么,在讨论批评的功能时他则有意无意地滑向了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含意缺失的展厅中,批评何为?》一文从语式上看是对海德格尔《诗人何为?》一文的模仿,但其理论意向却是德里达式的,在这篇主要讨论批评位置的文章中他沿袭了他所虚拟的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斗争逻辑,认为不可理解性是艺术态生存的合法依据,而批评的任务则在于解释和理解(无论以何种方式),所以它是“维持艺术态的死敌”,在这里,艺术史变成了抵抗解释和寻找差异的历史,无论在古典时期、结构主义时期还是在后结构主义时期,批评总是企图给艺术话语 “捆绑上一个含意”、扮演着“招安”的角色,而“艺术品被附着以一种含义后失去了对思维定式的批判力,这就是艺术态的瓦解和沦丧”,他认为写作不应是对作品加以释义,而应是摘除对作品的各种释义,他称这种写作或批评为“解批评”,它的功能在于保持文本的“可死性”和不断创造它的“可创性”,“释读机制是艺术态生效的前提,而释读的最终得逞是艺术态的沦丧”,从这种逻辑出发,他承认一般释读,而反对专业释读,在他看来前者是作品生效的引子,而后者则是作品沦丧的原因。这样,他就既为读者的存在留下了一个脆弱的依据,又为批评家与艺术家的现实关系找到了一个可怜的理由:“批评从来都是以扮演敌对者的方式对艺术做出贡献。”{邱志杰:《在含意缺失的展厅中,批评何为?》,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3期。}
王南溟也力图以语言学逻辑解释艺术史的发展,但与邱志杰不同,他不仅同意易英艺术意义由模糊到明确的历史发展的观点,而且进一步强调了艺术语言和艺术意义与艺术情境间的动态关系。他认为,从艺术史角度看,在现实主义时代艺术意义中所指与能指关系是对应的,在浪漫主义时代所指和能指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能指是被创造的,而在观念艺术时代,艺术所指是“超级的”,“艺术仅仅被能指所给予,艺术由现代主义的所谓创造性(原创性)的艺术步入意义的艺术(但仍然是形式主义的)”,“检验艺术的是形式文化”,艺术从创造到意义虽然是以能指的差异性为原则,但“文本的意义系于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并与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发生关联下获得意义……能指总是一种意义可能,一个形式的意义依据于形式的观念场”{王南溟:《观念艺术:艺术从创造到意义》,载《江苏画刊》1994年第12期。},他还论证了现代主义以陌生化为特征的“意味性形式主义”与当代艺术中与社会文化政治问题情境相关的“观念形式主义”的区别,两种形式主义批评导致不同的关注对象,即“好画家”和“有意义的画家”。所谓艺术意义由模糊到明确,实质上即是当代艺术由“意味的形式主义”到“观念形式主义”,“当代艺术使意义从无意义形式主义的差异层面进入能指与具体语境层面清晰性意义之中”,艺术意义是设定的,在能指嵌入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之中被理解,而艺术的批判性正是在这种从语言学到社会 —文化—政治学模式的转轨中呈现出其“新的维度”,当然,他也谨慎地强调了他所谓的“意义”与易英所谓的作品“含义”之间的区别:“这种‘意义’的艺术不是向‘含义’的艺术的回归,因为它仍然在形式主义中,像‘意义’的形式主义区分了‘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一样,这种意义的形式主义区分了实在论的现实主义……它并不像实在论的(如易英所认为的)对意义的理解,企图将作品的‘意义’回到明确的所指中,即离开上下文,离开语境,其意义就能确定。”{王南溟:《“片断”的观念形式主义:“后现代”之后》,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4期;《意义的设定:从解构到批判》,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12期。}与邱志杰对批评的敌视态度不同,王南溟肯定了批评对“观念艺术”中观念的“审查”作用,他认为与“表现”时代艺术理论无法干预艺术家的状况不同,“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已经完全改变了理论的身份,即理论总是冲击着艺术而不是尾随着艺术……艺术理论与艺术品同样重要或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正是某一时期的某种理论给定了非艺术的事实为艺术,而且艺术随着这种给定的变化而变化。……艺术能指的差异性就在理论与理论之间……他要求艺术家另外增补更为至关重要的能力,即艺术的理论分析。这样,艺术家一身兼两职——艺术家和批评家”{王南溟:《观念艺术:艺术从创造到意义》,载《江苏画刊》1994年第12期。}。
与王南溟相同,沈语冰、周宪、高世名、王林、马钦忠等人也围绕“意义”问题以语言学的方式介入了这场讨论,但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对邱志杰“批判形式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提出挑战。沈语冰在肯定了邱志杰对“表现论模式的现实主义批评”的同时,指出邱的形式主义依然是结构主义方式的形式主义,而且有由左的方向滑向解构主义的危险,他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就必须来一次批评话语的转换”,他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语言(词)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 的原理,认为对艺术意义的研究必须由“语言学”的研究转换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艺术语言的意义讨论将让位于对艺术话语的有效性主张的关注;对作品意义的解释让位于对当代艺术中的个人话语的聆听;现代批评家对作品意义解释权的可笑垄断将让位于批评家与艺术家围绕作品所进行的对话;一句话,我们对现代主义理论中那种冷冰冰的艺术语言系统或结构的关注将让位于对具体的艺术话语的交际实践的兴趣。”他还认为“意义”只能产生于主体之间【inter- subjective】被述说、被指认和被否定的关系之中,“没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也就不会有‘意义’”{沈语冰:《从语言的意义到话语的有效性》,载《江苏画刊》1995年第7期。}。他还指出,意义问题讨论的核心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的问题,“易英的‘意义的明确’似乎只能导致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粗浅图解艺术……而邱志杰的‘批评形式主义’……只能导致毫无指向的伪艺术的大量衍生”,“语言唯我论”与艺术形式的“陌生化”理论都忽略了艺术存在的方式和人们经验艺术品的方式都是非语言的这一事实,而“艺术批评意在把一件艺术品产生的特定条件、情境和意向尽可能地揭示出来”{沈语冰:《语言唯我论与陌生化的歧途》,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4期。}。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