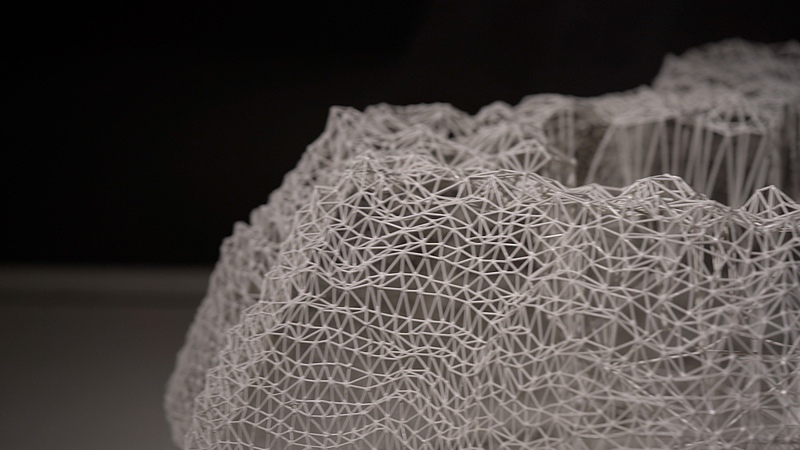范曾:是那时候醒了,还是闹钟给闹醒的?
范曾:这个几十年了,它已成为条件反射了,不需要动静来喊醒我。那么过去王国维,他说自己必须每天两小时,绝不能动摇的一定要看书。他的学问之大,当然,我说是近代第一人。他的积累是持之以恒,当然他不是每天仅仅两小时,是最低限度。那么我之所以五点钟起来,我把王国维这个最低限度早晨完成,那么其他时候也可能,我今天写文章看书六个小时,这都是很多的。可是这种坚持非常重要,一个人记忆力可能有点差距,这个差距也是可以补偿的。你们知道《秋兴八首》里有匡衡抗疏功名薄,这个匡衡就是记忆力不太好的人。结果人家念二十遍,他念二百遍。所以讲抓紧时间,尤其年轻一代的人,不要虚度。
范曾:有什么问题要跟范先生交流吗。
蒋步葛:我们时代呼唤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作。请问范先生怎么处理好人品、诗品和文品的关系,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范曾:这个诗人是呼唤不出来的,就像大师呼唤不出来一样。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忽然冒出个人,这人行了。你说在黄宾虹七十岁以前,再呼唤他 他也出不来,可他占了个长寿,到了八十岁,辉煌;到了九十岁,不朽的大师。我举黄宾虹的例子就是要告诉年轻人,不要太急于地给自己定个什么指标,哪一年我成名家,哪一年我成大家,哪一年我成了大师,做不到。你越不想这个东西,可能它会接近你;你越想它,你本身就不是内美修能了。所以说我们平心静气地、孜孜矻矻地、朝斯夕斯地、念兹在兹地从事我们所喜欢的事情。记住八个字:一息尚存,从吾所好。
主持人:好,这位女士,您有请。
张淑琴(北京市朝阳区诗词研究会《雅风》副主编):范老师,你好。我的年龄已经七十二岁多了,这种年龄又没有文学的基础,怎么能进入诗词的殿堂?
范曾:中国诗词的殿堂是敞开来,向所有年龄段的人、所有学历的人、所有经历的人,没有讲可以不可以进,这不存在。这个需要自己花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孔子五十岁开始读《易经》说明他很努力,按说像孔子这样的人应该知道《易经》是多么重要,是五经之首,他五十岁开始(读)。我想艺术对我们来讲,不像《易经》那么沉重,它会使你在游戏的状态中渐渐深入,可是自己不要对自己提出太过高的要求。你比如讲,我现在范曾,我想做芭蕾舞演员去,那空生烦恼了。所以还是游戏之状态,忽然说不定哪天出一首大家认为极好的诗,这个就是不可预料的。我希望你写得越来越好。
张淑琴:谢谢。
主持人:我们台湾的同学和老师们有跟范先生交流的吗?
陈佳好(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学生):范老师您好,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要诗歌创作,除了在秉持着本真之心之外,像有些诗人创作是十分呕心沥血,可是有些人却能够信手拈来。我想如果我们一般人想要尝试的时候,范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谢谢。
范曾:过去贾岛作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三年熬出这两句诗,别人一看就流下眼泪。那么我想这个是极而言之,就讲作诗有快有慢。你像祢衡,这《三国演义》诸位看过,到黄祖那儿,在宴会上写出一篇《鹦鹉赋》,我相信写得出来,叫我现在去一个宴会,三个钟头,我写不出一首短赋来才怪。因为你们看我的《急就章》都是不超过三十分钟写出来的,等稿子的编辑在旁边,提起毛笔来写。当然不是对群众不负责任,如果讲范曾那么对群众不负责任的话网上早骂开了。这个有一种神圣的自尊,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才思敏捷。作文章有快有慢,司马相如写文章慢,拿个毛笔尖含在嘴里,一直到毛笔尖都腐烂了文章还没写好呢。他不是大文人吗,也是大文人,我们看的是结果。你又快又好,当然高;你慢而好,也好。不过像这个司马相如吮笔而毫腐,像贾岛两句三年得,这都是极而言之。我们不要太相信古代文人最后发清狂的语言,讲李太白一定是醉了以后写的诗,我完全不相信。就像画画一样,画画也有快有慢。李可染先生,我的恩师画画就非常慢;南京一个大画家傅抱石,画画非常快,这个不重要重要,艺术是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