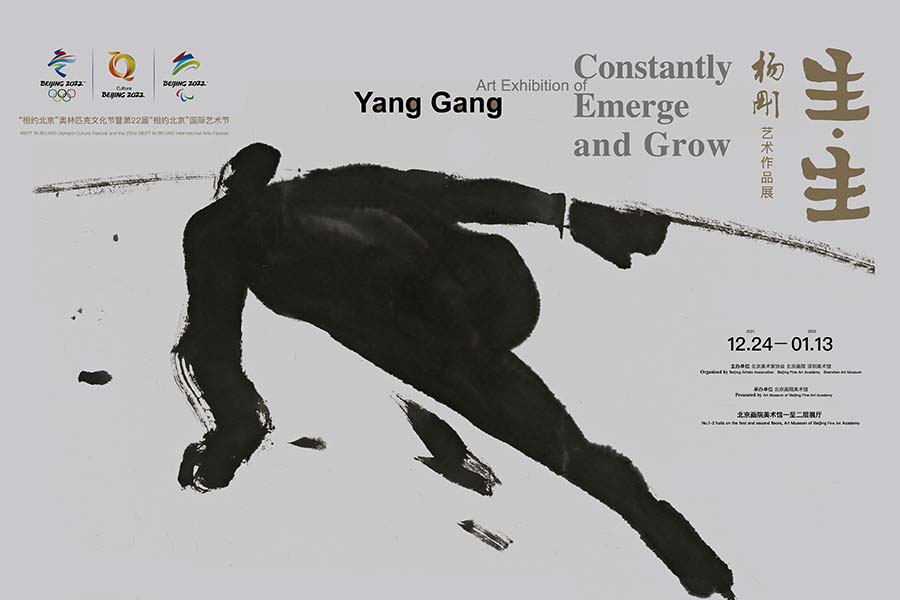问:您读博士是跟着哪位老师?
答:田自秉先生。我没有读过硕士,工作了四年,我读博士的时候,1991年我应该是副教授了。我做了三年编辑以后,因为是系里出去的,就已经在系里兼课了,所以虽然我的编制在《装饰》杂志,但是我已经是史论系的老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想读书,因为我比较成熟了,不可能再去读硕士,所以就想去考博士。当年是田先生招,田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我就去报考他,是在职读。我是1991年考进的,到1995年1月才毕业,读了四年。1999年,我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第一届评选,每年评百篇。我那年又容易又难,难的是前面攒了好几届博士,过去都没评过,所以参评的基数比较高,参评的人比较多;容易的地方是,那会儿大家都不知道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价值,评不评上都无所谓,所以稀里糊涂就提交了,稀里糊涂就通知我评上了。评上了以后,因为当时不像清华,清华评上的学生和导师都有奖励,工艺美院对这个事也无所谓,评上了就评上了,导师也没奖励,我也没奖励。
问:您一直就想走学术之路,后来就当老师了吗?
答:我毕业以后,本来是浙江美术学院要我,但是当时这边的何燕明老师把我留在《装饰》杂志当编辑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没有一下子留在系里是非常好的。因为《装饰》杂志是一个很特别的杂志,它是全国性的刊物,后来才变成学报。1958年创办的时候,它是跟《美术》杂志齐名的,当时的编委都是全国的编委,像沈从文、丁聪、沈福文这些都是编委。这份杂志全国的同行都很认,何先生把我和邹文老师留在《装饰》以后,就带着我们全国各地去组稿,认识全国的一流专家,这对我们开阔眼界、增强学术的判断力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问:看来您在《装饰》有很大收获。
答:我们在《装饰》到什么程度,因为当时学校里有两刊一报,报纸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刊,就一张,像《北京晚报》那么大小的报纸,那是何先生带着我们创办起来的。两刊,《装饰》和《工艺美术参考》。当时人很多,发稿量也很大,我和邹文老师在铅排时代,就是用镊子一个一个夹起铅字来放在一个版里面,怎么夹过来排,哪个垫高一点,哪个中间要加一个插图,边上哪个地方要塞一条缝,给它塞紧了,我们都会操作。后来,王选最早的激光照相制版,我们又做过,所以我们经历了中国现代印刷的几个跨越。记得我和邹文老师两个人骑自行车,从工艺美院骑到通县管庄五里桥,在冬天骑两个小时去印刷厂改版。回来以后在路上的小饭馆吃羊肉火锅,那个很好,那会儿也年轻,骑车也不怕。实际上冬天骑两个小时,来回四个小时,那真是不容易。
问:我记得当时采访何燕明老师的时候,他也讲到因为自己性格特别耿直在特殊的年代受过牢狱之灾。我的采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当时太年轻了,充满了那种惋惜的感觉。他可能是觉得耽误了好多青春和时间。
答:我觉得他一点都没耽误,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耿直,在那个时代也苟活着,苟活着有什么价值,有谁像何燕明先生那样,六十几岁了还能重新出任《装饰》主编,带着我们把这本杂志办得风风火火。我觉得他六十几岁,这十年就顶得过别人的三十年、四十年,他有苟活吗,他一点都不苟活。别人整天在家,整天端着茶杯,上着班,那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两样。
问:我写完给他看,他肯定很高兴。因为他觉得,在被禁锢的过程中,他不能干他自己热爱的事情,所以他常常说的口头话就是“能工作就好”。
答:何燕明先生把我们当成他的孩子,我在内心里也是把他看成父亲,真的是有这样的感情。我现在从外地回来,我第一个要去看的人是他。我要不去,他就会想我,他就会惦记,会打电话说,你现在在哪呢,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他和孙老师,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对我也非常好的老师。应该说除了大学四年,我踏入社会真正的引路人是何燕明老师,他带我去见艾青,他带我去见曹辛之,著名的诗人,九叶诗派的。他带我去见了万曼,著名的保加利亚壁挂艺术家、纤维艺术家。他带我见了很多人,全国各地跑,他那时候六十多岁了。
何先生是个诗人,他当年是写诗的。他是国立艺专雕塑系毕业的,受到打击的时候那么困难,他就捏泥人卖钱来养活他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有出息,女儿是教授,大儿子是原来北京工艺美院研究所的所长,二儿子是著名导演。
问:您留在系里了,就一直从事教职工作?
答:我是1994年做《装饰》杂志副主编,1996年做主编。1999年,工艺美院跟清华合并,我觉得我在《装饰》已经不可能干得更好,我在的时候《装饰》已经获得了期刊的最高奖——中国期刊奖,所以我也不想再干下去了。这时候系里正好需要人,1999年我就先到系里来,但是那时《装饰》主编我还兼着,因为当时一下子没有找到人。我到系里先当常务副主任,刘巨德老师是主任,他们觉得史论系主任,我这个岁数好像太年轻了,2000年我39岁。我到系里主持工作的时候,除了邹文老师、杨阳老师是我的同学,其他的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就想找尚刚老师做我的搭档。2001年,我从常务副主任升为正主任了,我就向学院提请,请尚刚老师出山,做副主任。
我跟尚刚老师干得真是高兴,当时系里有些新气象,他们都很怀念。李静杰老师、陈岸瑛老师、张敢老师、岛子老师,都是我和尚刚老师在系里做主任的时候调进来的。所以现在我和尚老师很自豪,我们引进的人才,现在有副院长,有系主任,有著名学者。
2003年,我已经在系里做了4年系主任,我又觉得我已经不能继续干得更好了,这时有个机会,李嘉诚基金会上清华来,想借我去到汕头大学创建一所设计学院。当时我也有经济压力,因为曹老师要去英国留学,我们又买房子,要按揭,李嘉诚基金会给我开出的年薪是很高,足够我解决以上困难。
所以我就跟学校提出去汕头创办设计学院。清华校务会议专门通过我的借调,但没有同意4年,只同意借2年,2003年到2005年,2005年回来闲了一段时间,没什么事,因为他们还想让我继续干系主任,我说我坚决不干了。2006年我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了半年的高访,2007年回来, 2008年做副院长。
问:您当主任的时候调人才是什么思路,怎么引进的?
答:当时我和尚老师有两个意见,非常一致。一个是我和尚老师到系里组织工作的时候,系里的这些老先生正面临着更新换代,老的基本上已经退了,那会儿尚爱松老师、奚静之老师、叶喆民老师、田自秉老师、王家树老师全退了,这一代人在系里也面临着要有接班人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希望,原来工艺美院的体系能够进一步的充实,在继续保持原来工艺美院史论系特色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学术眼光,需要根据我们系里的学术发展的布局来引进人才。比如西方美术,奚先生和吴先生退了以后,西方美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另外一个是中国美术,原来通史是我们的优点,但是书画、卷轴画或者宗教美术是我们的一个弱点,所以当时我们要了研究佛教美术的李静杰老师,外国美术方面要了张敢老师,因为张敢老师是邵大箴先生的博士,是做西方研究起家的。
问:您刚才说有两点和尚刚老师一致,一个是保持传统,一个是开放学术。
答:还有一点是我们强调,我们引进来的人,人品一定要好,人品跟学术一定要兼重。我可以举个例子,当年向我们递材料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些也是在美术界有影响的人物,给我们递材料,我跟尚老师一看,某一位一年写了十几本书,我和尚老师一听就说,这样的人我们不敢要。
问:您当副院长期间主要负责哪一块?
答:那时候负责科研和美术馆,我最初负责过一段时间的外事,后来赵萌老师回来了,就把外事交给他,我主要负责科研,科研主要是纵向课题、横向课题,还有社会服务。美术馆主要是,把美院B区展厅打通改造成一个美术馆,原来就是一个临时展厅。我们当时特别精心地来做这个事,记得当时学院美术馆正式挂牌成立,请马泉老师做logo和整个导视系统。第一个展览就是美国哥伦比亚现代版画展。
科研管理方面,原来美术学院一直不重视做学术,因为大家都认为画画好、设计项目做好就行了。但是因为并入清华以后要做研究性的大学,所以学术研究这块,不单是做史论的人,其他专业的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做科研副院长以后,提倡这个事,鼓励大家积极去申报国家的重点课题项目,做了一些工作,而且比较有成效。我第一年做科研副院长,因为国家社科基金我是评委,所以我们就争下一个全国重点、五个一般,那是学院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清华都很震动,感觉到美院很厉害。我和尚老师应该是在学院里面获得各种学术奖比较多的,北京市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我好像得过三次,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还有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我得过两次,第一次尚老师也得过,是我和尚老师。
问:2011年举办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的时候,您是负责人。
答:我在任期的后面主要做设计三年展。我的任期,一个是改建了美术馆,然后做了一套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老先生一人一本,做了一个三年展,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一点事。
问:对转型这个事,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答:因为高校里面的艺术家、设计师和社会上的艺术家、设计师是不一样的,社会上的可以由着性子来,可以寻找你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高校里面的艺术家、设计师,首先是个教师,同时是个研究者,第三才是艺术家和设计师,所以你不能忽略前两者的身份。
问:您的性格,从大学一直就是这样很直率、很敢说的特性?
答:当然一直这样。这是义乌人的性格,我必须要强调一下,什么叫义乌人,唐代的骆宾王是义乌人,宋代的宗泽是义乌人,写《海瑞罢官》评价的吴晗是义乌人,当时鲁迅跟我党接触的最重要的朋友冯雪峰也是义乌人,后来也因为耿直被打成右派。所以义乌人天生有一种倔,义乌人是有所坚持的。
问:您是骨灰级系友,说说您对系里发展的一些建议,还有寄语。
答:对,骨灰级,骨灰级是最厉害的,是吧。系里未来的机会应该挺好的。因为咱们系对清华的体制是比较适应的,清华也比较认咱们系的发展,属于是高校发展的,研究性大学发展的主流,所以咱们系可以是大步向前。
另外,这里面可能要实现一些转型,我觉得老的要守住,也就是艺术史学里面我们工艺史的研究,这是咱们系最有特色的,如果老的不守住,作为一个艺术史论系来说,是没法让大家尊重的。所以艺术史学的工艺史研究要继续守住,要发扬光大,要做大。
还有就是当代这块,艺术史、艺术管理或者艺术理论在当代新的出现的重点和趋势,我想是我们应该很认真地去注意它,因为你毕竟不是真的是象牙之塔。世界上的艺术教育,其实格局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当代艺术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能跟更多的人产生关系,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启发或者感到有用的话,这很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在追求我做的事一百年以后再有用,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要有一个好的格局,既要有我们的坚持,就是传统的优秀学科的坚持,也要面对当代艺术与生活的新趋势,关注和观察它们的发展。
问:现在系里引进了艺术市场,还和经管学院合作,您怎么看?
答:很好,但是要做就得做大,别浅尝辄止,要更加努力去做,要做得更大,而不要大不大、小不小,别满足于我们有就行了,我填补空白了。你要做就做大,要做得比央美还有特色,比央美还有影响,得想一下我们怎么做,这里面有策略。你并不是要跟着央美屁股后面跑,艺术市场多大,任何一件事情,实际上只要你意识到了去做都不晚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做。如果觉得晚的话,你想圣贤以后还有活着的必要吗,我们还得活着,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前进。
问:系里发展还存在什么问题,您有什么需要指出的?或者是对学生的一些建议。
答:一个是要多引进人才,还有一个是在招生上,我希望能够招到真正对艺术史论有兴趣的学生。
问:您现在在杭州工作忙吗?
答:很忙,我在中国美术学院那边也负责全校的科研和四个博物馆。
问:您就是喜欢这种马不停蹄、永不停歇的感觉。
答:不是喜欢,而是我认为,人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如果想追求不朽,人的生物生命是有限的,大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会到来的,我只有通过努力多做事,来追求我自己认为的不朽。这是我的信念所在,实际上谁不想享福啊,谁不想在杭州的湖山之间喝喝茶,散散步,走一走,但是我觉得趁我现在还不算老,还能干得动,就尽可能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好事,能留下来的,这是我认为的不朽。
采访:梁开撰文:梁开、郭秋惠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