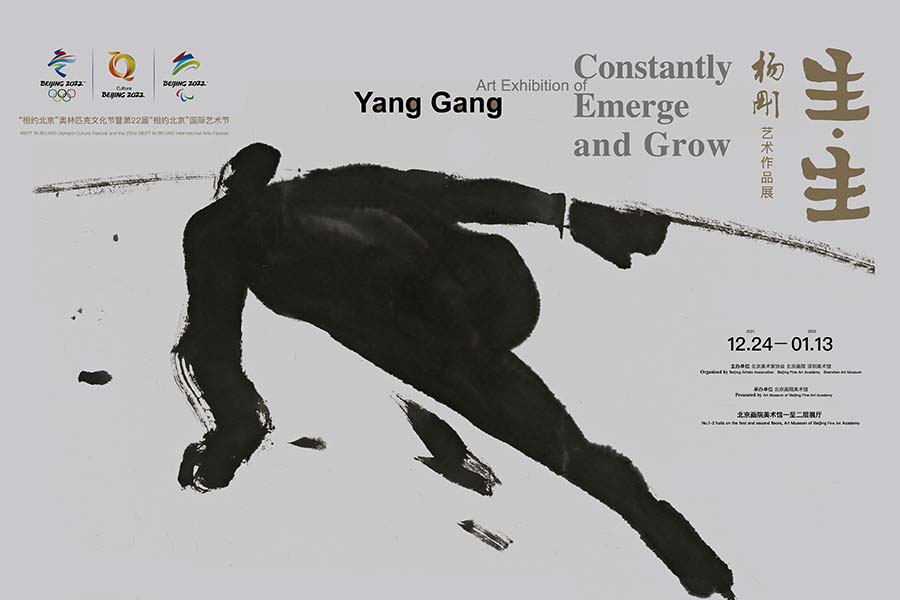83班杭间学生时代(在八楼宿舍门口,门上有室友姓名和手印)。
问:在这些课中,您对哪些老师印象最深刻,觉得对您有很大的启发。
答: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四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王家树先生,王先生给我们上工艺史,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非常注重学生思维的激发,他有一个做法:每段课讲完以后,让每个同学写一个小纸条,谈你对这个课某些东西的想法,他要鼓励你们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新的,不同意他的,也不同意所有教科书上的,哪怕你们不成熟。所以当时在这个课程上,我们都争先恐后,挖空心思想新思路,这是我们早年教育都没有的。所以王先生这门课,虽然它是系统性的,但因为王先生讲课,讲着讲着就信马由缰,跑得很远,所以整个教学任务其实都没有完成,都没有讲完,但是我觉得就凭这一点,已经让我们终身受益。
第二位老师是李永存老师,虽然我们很关心当代社会的发展,但是毕竟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小地方来的,李老师以整体修养以及艺术眼界让我们这些从小地方来的人真是大开眼界。尤其他请了那么多不同领域的老师来做讲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构。
第三位是奚静之老师,奚老师的口才很好,加上她非常和蔼可亲,再加上她对苏俄美术非常熟悉,她真是像涓涓细水一样,听她的课是非常好的享受,因为她讲的思路非常清晰。这三位老师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体会到的好。
还有一位老师是我们很多年以后才体会到好,就是尚爱松先生。尚爱松先生是李泽厚的老师,他的学问太大了,修养太深了。他上课讲的,我们这帮小孩听不懂,尤其尚先生讲课有一个特点,他很放松,没有什么提纲、教案,就是讲,通过很多的掌故,他的同时代人,比如胡小石怎么说,傅斯年怎么说,比如对吴道子的问题,对美术史上的某一个问题,他引经据典,各家的观点,而且那几家都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是跟他有很多交往的,说着说着又说点这个人的轶事掌故,所以我们听着天花乱坠,但是因为没有很深的知识储备,当年听得似懂非懂,事后才知道尚先生的好。这四位老师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至于田自秉先生,因为当时他是副系主任,平时和上课都不苟言笑,所以本科阶段印象不是很深,到了我的博士阶段,跟田先生做研究,才慢慢体会田师的学术的远见和博大,还有他的治学的严谨。
问:您觉得经过这四年的专业学习,您有怎样的收获?
答:我们那班的同学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外语数学不好,所以没有考上那些好的文科大学。我有一年高考落榜,高考落榜的原因是,我数学考了11分,但是我的语文、历史、地理加起来,比我同学考上北大的分数还要高。包括邹文老师,现在西安美院史论系主任赵农老师,至少我们三个人是数学不好成为高考落榜生。我们这些人在社会上也略有工作经验,知道自己怎么学习,课堂是一个方面,但我们知道自己如何去看书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当年咱们系初创,学院老先生和系里老师对我们真是爱护有加。庞薰琹、雷圭元先生都经常到系里跟我们座谈、聊天,而且当时整个艺术界的形势也很好,因为我们不久就赶上八五美术思潮了。我从八五美术思潮就开始参与《中国美术报》的编辑和发文章,其中最早提出对工艺美术在现代的困境引起争议的一篇文章《对“工艺美术”的诘难》是我1986年写的,那时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当年很有名的一本杂志《美术思潮》,湖北办的,当年在美术界影响最大的两份刊物,一份是《美术思潮》,一份是《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是1987年停刊,有终刊号,红的封面,里面弄了很多的一个一个的人像,那些人像都是它的重点作者。在终刊号上有我的人像,当年我还是四年级的学生,就已经被他们列为当代美术的重要作者。这个杂志在档案里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当年有条件来积极参与当代的八五美术思潮的一些事情。当年是有非常明确的发展线索,大家都是理想主义,都是充满热情。
问:您当时为什么能够参加这么多文章的撰写还有思潮当中去?
答:有的也是一些偶然的机会。当年在班里,我、邹文老师、赵农老师,我们三位因为原来文学的功底比较好,参与社会的意识也比其他年龄小的同学要强一点。现在系史应该提到史论系的第一份学生刊物《工艺美术史论》,我不知道系里还能不能找得到,是我发起的。当年那份刊物我们是油印的,打字的,我们请人打字,请人设计封面,一共办了十来期,后来传给85级那一班。我当时为了发起这份刊物,王家树先生介绍我去找庞薰琹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到庞薰琹先生的家,在他和平门的家里跟他谈。老先生那会儿已经七十多了,对我非常好,很认真,很郑重其事地对待你,给你意见。我在微博上也发了对庞先生这段的回忆,这是让我终身难忘的。
我和邹文老师在大一的时候挺有干劲,我们两个人用自己的诗歌、散文、小说办了一个墙报,全部是手抄的,我们自己设计刊头,还请那些画画的同学做插图。当时各系的同学都来看,当时影响还挺大。但是这件事情也给我们带来风险,学校里很多人就议论,这两个人还在弄文学,对史论的专业不专心之类的。
问:你们那时候除了专业以外,有哪些课外活动?
答:课外活动,打球,我还曾经参加过摔跤队,当时赵健老师是摔跤队的业余召集人,我到他的摔跤队是因为摔跤队能够发一双球鞋。球鞋发了以后,参加了两次就不去参加了。最值得说的是,我们老师经常组织我们去考察,我们考察得挺多的,像北京丰台的大葆台,蓟县的独乐寺,山东的曲阜龙山文化一带,江浙的园林,还有西安、甘肃、敦煌一带,我们基本上全部都走遍了。我们去蓟县独乐寺就是尚老师带我们的,我们到敦煌的时候,已经没人带了,就我们自己了,因为已经三年级了。这个考察生活,对我们做史论研究的人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我们当年画画也是老师拉我们出去写生,经常去房山十渡写生色彩,一去就是四五天,住在大车店里面,挺有意思。
到二年级以后,我的业余生活基本上就脱离集体了,因为我跟曹老师谈恋爱了,基本上就我们俩在一起活动。但是当年不让谈恋爱,团组织、班组织经常开会要“整风”,哈哈。
问:你们的压力很大。
答:压力很大,当年连老师也不看好我们,所以现在同学见面常常感慨我们不容易。
问:谈到写生,当时班里的同学都会画画吗?
答:我们班17个同学,只有两三个同学不会画画,其他的画画挺不错的。我们当年就很明确,招生一个是文化课要好,一个是画画要好。现在邹文老师还能做雕塑呢。
当时我们班有几个人画得不错,杨阳、曹小鸥、郭元平这三个人比较突出。其他人差不多,有几个不会画的,那我就不说了。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