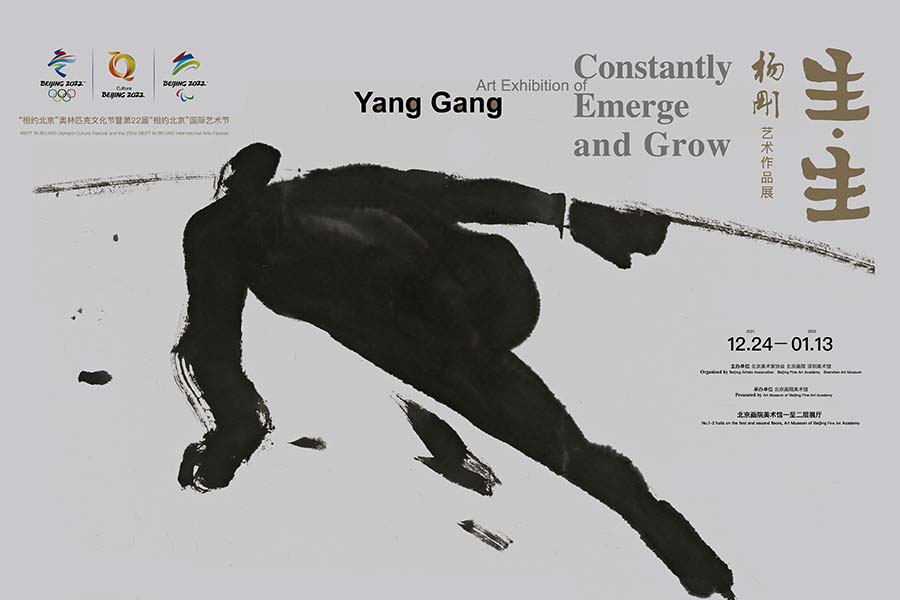云门的舞者不跳舞简直就不知道要干嘛
B:我听说有一次在《行草》演出之前,你把整个结构都调乱了。
L:我经常做这个事。
B:那舞者不是很崩溃吗?
L:不会,他们很厉害。他们自己整理一下,念念有词,自己负责。他们不是学生了。
B:这也是成为云门舞者的必要因素吗?
L:也不知道。慢慢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大的带小的,等你成熟了以后,就自管自了。跟他们工作是非常幸福、非常愉快的。
B:感觉你们特别像是公社。
L:也不完全一样,大家私底下还是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的确是比家人多,因为我们不断地在旅行,大家彼此了解、互相支持。云门的舞者常常必须把一支舞教给一个年轻的舞者。在一般的表演团队里面,这等于在培养一个竞争者。可是云门的舞者非常无私,而且他们会变成像一只母鸡一样一直盯着小孩好起来,不会怕这个小朋友取代他。
B:怎样的人可以成为云门的舞者呢?
L:基本上高矮胖瘦我都喜欢,当然要有一些基本的身体素质,但是我也特别渴求他的动作有个性。云门的舞者在做一致的动作时非常整齐,可是其中有很多不同细节,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我要保留这些东西。
云门的舞者必须非常喜欢跳舞,不跳舞简直就不知道要干嘛,他必须要喜欢云门的舞。云门的舞者要学很多东西。一般来讲,芭蕾舞者就学芭蕾,现代舞者就学现代舞,唱京戏就学那些身段。云门的舞者统统要学。最难的事情是,云门的舞者刚进来,大概经过两年时间才会有角色,才能完全掌握云门的语言和动作的方式。
B:在云门的作品中,经常把实物搬上舞台,比如说真的花、竹子。为什么?
L:在剧场里面,真的东西所幻化出来的精神跟道具是不一样的,像《流浪者之歌》里的稻米。我爱用这些东西,给技术组带来无尽的恶梦。
B:你没有用过动物吧?
L:用过。我有一个舞叫《梦土》,最近比较少演,里面就有差不多十来只孔雀。要有人养,旅行的时候,它们有专车。它们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很美。当它走进一个特殊灯光里,哇,那真是太神奇了。但是很麻烦,因为它们会大便,这个没办法训练。
云门舞团基本上终年都在募款
B:据说云门很穷,穷到什么地步?
L:这不是我的问题。其实美国的那些大师们每年也在募钱,交响乐团也募款,因为国家不养。云门舞团基本上都是终年在募款,道理很简单,因为表演艺术是劳动力密集,工资就占整个支出很大的比例。它不像周杰伦灌CD,作曲、录音、广告花了钱,然后就能大量复制。表演艺术最动人的地方是不能复制,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美国有一个公式,就是说政府的补助占33.3%,民间的资助占33.3%,自己赚33.3%,这是最健康的。可是我们政府的补助最多占到15%,我们就必须去赚钱,演出赚来的钱大概就高达50%,负担很重。民间的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去经营,要去跟人家来往,永远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但是现在我必须说已经很幸福了,早年真是很惨,一天到晚在烦钱的事。
B:你们的演出票房一直非常好。
L:大家觉得我们的东西看得懂,也许觉得很好看。我们团最近第一次在台湾演完后的谈话,大概有一千多人留下来跟我们对话。我吓坏了,有一点点吃惊。有一千多人问问题,问个没完,从半小时变成50分钟,变成一小时。台湾最近出了一本蒋勋老师写的有关书法的书,三个礼拜里面卖了三万本。销量吓死人。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对文化的渴求是非常强烈的。
有些东西不该忘,但往前走也很重要
B:台湾这块土壤有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这块土壤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L:有完全的影响。台湾的好处是,它非常小,但也很丰富。举个例子来讲,从我家出去,大概坐车20 分钟,就到海边,10分钟可以爬山,20分钟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一小时就可以到原住民部落。这样一个很稠密的多元文化的现象,文化的底蕴冲击着我们非常厉害。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各种文化之中。外来的东西很快被流行、被吸收。
另外一方面,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的政治上的改变是惊人的。这些政治的改变都使你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台湾曾经长期戒严,而我在戒严11年之后才编出《水月》,我的身体在戒严后才得到解放。以文字来讲,戒严完了,报禁没了,拿着笔就可以写了。但是身体是很奇怪的,对于跳舞的人来讲,身体的解放才带动你头脑的解放,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我要讲的是,这些政治上的变化、局势上的改变都在影响我,我在这里坐捷运、坐公车、坐出租车,我没有自己的车子,我活在整个社会的氛围里面。这些不一定会变成创作的题材,但这就使你的感觉、触感不一样。
B:你坚持云门舞集代表中国文化,你如何理解中国文化?
L:我不觉得我是要宣扬什么。云门是一个没有艺术政策的团体。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的好奇和喜欢。不能说你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就在你身上,它是必须学习的。我的作品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书法,我书法写得很烂,但我非常喜欢书法的美,简直是赏心悦目。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来看去。直到现在,我的书桌、床头、马桶旁边都有一些书。我进城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拐进故宫博物院,呆个20分钟,只看一幅字、一幅画就走。很多人进了美术馆以后,好像进了大卖场,头脑混乱。我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今天想看什么东西,就过去看一下。有一天突然觉得,“哎呀,书法也可以变成我们舞蹈的一个方向”,而不是说为了要做《行草》三部曲,去采风、搜集材料。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制作”,我做不来。
B:在你看来,究竟什么样的才是中国式的作品,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
L: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是这样来做,但其实我有很多作品也非常欧洲风,因为我们每年去欧洲,当然也留下它的印记、触感、对美的感觉。所以什么叫中国?是云南还是北京呢?这是一个很泛的范畴。比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就是中国文化吗?当然是中国文化。但是中国文化有很多的面向。对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挑战是什么东西会被留下来。这是未知数,我喜欢把事情看成未知数,其中有无限的可能。30年代的文学留下来的、最打动我们的,还是鲁迅、沈从文。它是经过时间淘汰的,并不是预测性地做总结。
有时候我们喜欢谈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或者中国文化。我们向往这些字眼的时候,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框框?最可怕的是用外国人的观点来看中国,中国就是舞龙舞狮,就是麻将。我觉得那也是中国文化,但只有这些吗?有些东西是不该忘了,可是往前走也是很重要的。
三道坎
B:1988 年,你曾经想放弃《云门舞集》,那是怎么回事?
L:云门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顺畅,特别是在早期。1983年,云门十周年的时候,我创办了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同时做两件事情,当然做不好。80年代早期,我没有留下什么大的作品。我不知道把那些舞者拖下去,会走到一个怎样的山穷水尽的状况,也没有力气再去打点经济状况,所以我就停掉了云门。
B:去年,一把大火烧掉了云门的排练场。你在发布会上,还流泪了。
L:还好了,眼泪不成汪洋大海,两滴泪总有的。后来,从企业到国小学生,有5000多人为云门捐款。以前,我有时会想一想该退休了、怎么退休这个问题。现在,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我有5000个股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B:似乎看起来你一生中最大的坎,是因为受伤,放弃舞蹈,选择编舞。
L:受伤对舞者来讲是家常便饭。不是技术问题,这是职业的问题。那次受伤跟我放弃舞蹈演出没有关系,在那之前我就在编舞。我之所以没有再跳舞,是因为事情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上课。身体不行了,怎么表演?所以很自然地就慢慢地不跳了。但有趣的是,受了伤,才知道应该怎么跳舞。
年轻的时候,做不到的事情,愣是要做成。受了伤,你就开始第一次注意到你的身体,跟身体说话。因为你有伤,它迟钝,所以你要唤醒它,这是很有趣的。很多舞者受伤以后,跳得更好了,而且不再受伤了。
云门舞者的年龄从23 岁到43岁都有,还有三四位母亲,我很喜欢她们,好像她们生过孩子以后就懂事了,懂了很多妈妈以前不知道的经验。更重要是,她们对身体的感知度更加灵敏了。
年轻的时候就是要燃烧
B:你在平常的时候和在排练的时候,是判若两人吗?
L:特别是以前,我大声嚷、大声叫。我性子太急。更重要的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经验,我指出一个很模糊的方向要舞者做到,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经验多了以后,知道要怎样去达成,今天要求一点点,明天要求一点点,先做这个再做那个,所以相对就没有那么急躁。而且云门的舞者都这么棒,如果一个人今天老是做错了,那你跟他说了也没用,因为他今天就是不行,也许过两天,跟他谈一下,他一定是生活、身体上有了状况,我知道了以后就不会再强求。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强求,像电机似的,有按钮就要发声,这些都是不对的。
B:很难想象你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气,手砸在玻璃上,血流如注。
L:我想我现在还很冲动,我还是老愤青。但是有些事情的冲动是好的,有些冲动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年纪大了以后,冲动还需要花一点体力。
B:我们采访过《转山》的作者谢旺霖。你面试他时,问他“不害怕吗?”如果你面对这样的选择,或者说旅行的时候,你会自问这个问题吗?
L:谢旺霖做的事情,我不只是害怕,我想都不敢想。很多事情应该要害怕。我现在觉得,我们为什么觉得害怕?谢旺霖说得很好,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怕两样,一个是怕没有钱,一个是怕没有人爱他。
然后他说他旅行回来以后,没有那么怕了。人怕死,或者怕不成功,我现在比较好,不大在乎成不成功,反正成功也是继续忙下去,失败了,那就下次做好咯。对年轻的朋友,我想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做了以后再来反省、再检查,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很多人想了很多事情,从来不敢走出一步,因为太怕了。事实上是怕失败。可是谁成功了呢?
B:我想提到你的年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L:我62 岁。
B:你已经62 岁了,但一直这么充满梦想。很多人在讨论你的退休问题。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不是不存在?
L:不存在。因为我希望能把舞团内部的制度、人事、整个团队的素质提高,任何人来接我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比较上手一点,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哪里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走;我走的时候,身旁有哪些人可以接班。你不能这样想,你想了,也许那个人负担很重;也许你想了以后,他就走了。这是强求。但是我知道,等到有一天我退休了,云门如果有新的艺术总监,那么我们今天所谈过的这些舞大概统统会蒸发掉了。因为董事会一定会找一个有个性、有才华的编舞家来编舞,必须要找这样的人来接我的工作。新任艺术总监的方向和感觉就不一样了,他不用书法,他也不觉得一个人应该蹲马步。不蹲马步,没有这些基本训练,那这些舞就不能跳了,这是肯定的。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哀叹或者庆祝的。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