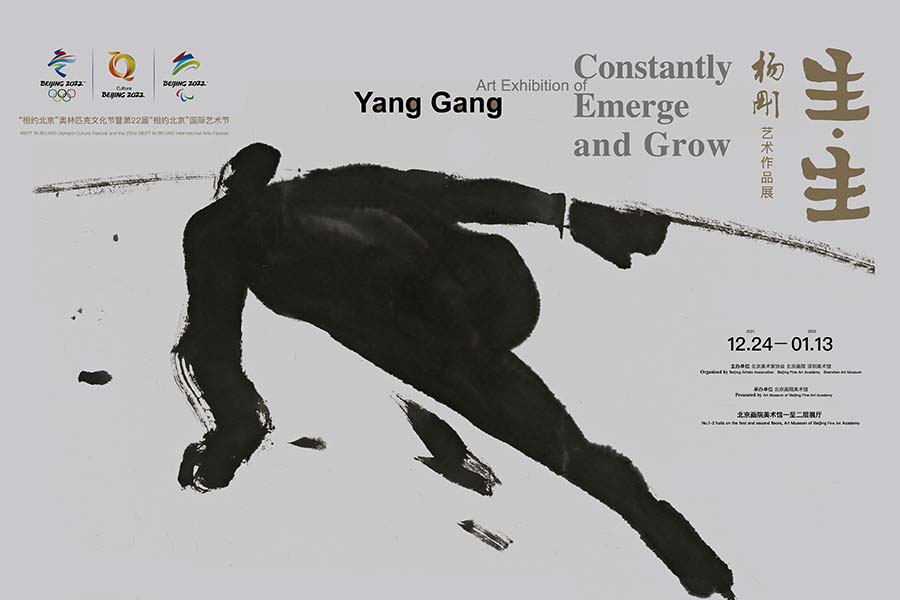文/刘莉芳
常说中国书法“龙飞凤舞”。林怀民从书法美学中汲取灵感,2001年编出了《行草三部曲》首篇《行草》。云门舞者用身体动作来临摹书法家的挥洒书写。11 月至12月,林怀民携《行草》进行内地首次巡演。11 月21-22 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11月27-29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演出期间,林怀民做客本报和上戏主办的“外滩讲坛”,并接受了本报专访。
11 月18 日,杭州一位媒体朋友在MSN上敲来一堆字,说,林怀民这三天在杭州,在小店里吃咸菜炒蘑菇,跑到灵隐寺里充电。
林怀民的杭州行是《行草》内地巡演的第三站,据说首场演出票仅剩32张。11 月19日,林怀民告别杭州,来到上海,遭遇浦东下午的塞车。
林怀民害怕塞车。原定20日的讲座,我们预备叫车把他从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接到到浦西的莲花路上戏分校区。他不肯坐车,坚持坐地铁,从二号线的科技馆站,倒一号线,到莲花路站。跟随他多年的佩贞说:“你别觉得怠慢了他,他其实怕塞车耽误观众的时间。”
林怀民在台湾出行没有私家车,捷运、小巴、出租是他的主要交通工作。前几月,他刚出门,一辆出租车从他面前开过,又“呦”倒了回头。司机说,我今天遇见你,一定要载你。台湾的很多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林怀民。林怀民说,“出租车司机的话,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分量的。他们不需要奉承我。‘总统’的话还不如他们。”
在云门创建初期,林怀民曾经历低谷,关闭云门。激励林怀民重整旗鼓,重建云门的,不是别人,却是出租车司机。“他们也许没有看过云门的表演,也许看过,可是他们把云门当个事,他们说,你们知识分子说了很多,该你干嘛的时候,你不干嘛,那不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十几个司机对林怀民“演讲”。“所以我就羞愧地夹起尾巴,重建了云门。”
林怀民是位演说家。不断听到朋友这么形容他。果然,我比预约时间提前一小时拨通他的电话,他的声音灌满了精气神,“你的采访提纲做得很好”,“你稍后一下,我抓个椅子过来”。过了几秒,林怀民回来,进入“说话”状态。
B=《外滩画报》
L= 林怀民
云门的舞是跟自己的身体说话
B:你曾说《行草》太规矩,对“伟大草书”过度敬重,有点像在练九宫格。这次内地巡演,会就此做些变化吗?
L:我说《行草》像练习九宫格,是说用一种很端庄的心情来做它。它的格律性高一点,形式上严谨,是这个意思。
B:你这次会在《行草》中加入更多的放肆、个性吗?
L:它的个性已经过度强烈了。《狂草》比较个性、放肆。有观众觉得《行草》太凝重。最近,《狂草》在台湾演完后,有一位先生说,下次再演《狂草》的时候要准备氧气筒,透不过气。可是一个年轻人说,他一辈子看跳舞,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没有一个舞能够让他看得这么畅快,他的身体快乐得不得了。每个观众都得到不同的东西。
对《行草》来讲,有人说太多了,有人说好丰富,因为这里面又有字又有舞又有音乐。
有趣的是,在国外演出的时候,观众完全没有负担,因为他们不懂汉字,更看不懂书法,他们就觉得好美。中国人总在想这是什么字?这是谁的字?看跳舞不是去考试,是为了感官上的经验。求知欲强烈,就会给观舞造成负担。如果觉得凝重,他大概是过度认真了。
B:和你这么多年的舞蹈语言从加法到减法一样,也许观众的观剧体验也需要培育过程。
L:我想可能。拿《行草》来讲,不是在表现或者表达书法。而是我们用对书法的情感来促发了这些作品。再说清楚一点,书法是《行草》三部曲的一个想象力的跳板。
2000年第一次演出的时候,观众写信来质问,说后面是王澍的字,但前面跳舞的动作像颜体。那他就很辛苦了。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在跳舞。要看字的话,到上海博物馆去看吧,那里收藏了很多很好的字。
观众也在进步,今天是一个视觉的时代,不再是文革时代—说错一句话,吃不了兜着走。
B:内地观众对你的作品的接受程度有什么变化?
L:我只求求大家不要开手机讲话,那我就很感激了。影响舞台上的舞者还在其次,对旁边的人是很不公平的。
B:云门的作品在视觉上很美,也有一些独特的舞台语言,但是之所以全世界的反映一致,是否是云门的表达方式比较本质?
L:我倒不一定有这么哲学性的内容吧。舞者们很好,他们做的事情很吸引人。云门很特别,除了自己的动作语言不一样,我们着重于传统肢体的训练,比如说拳术、气功、太极,我们学静坐、学毛笔字。一般的舞蹈都是外扬的、外塑的,让你感觉到很刺激,唯独云门舞者有一种特色,在台上把人引过来,他在为观众表演。因为整个训练和表演的方法是,你跟你自己说话,你跟你自己的身体说话,因为我们的整个传统是非常内在的,特别像太极,完全是气功,讲究怎么吐纳,再比如拳术,讲究你的身体内部如何缠撕,这是我们不同的表演方式。
B:这也需要观众跟舞台上的舞者共鸣,才能够欣赏这部作品的妙处吧。
L:那些跟观众没有关系。比如我们在台湾,一年里做好几场户外免费公演,也到农村去,观众里有小孩,但从来不吵,几万人,安静得不得了。所以是完全看台上的演出如何凝聚人心。
编舞就是要喂饱舞者
B:你的作品一直在做减法,你会减掉哪些东西,原则是什么?
L:编舞很有趣,好像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就东想西想吧。可是到了最后,我总想找到一个限制,用最简的因素,在这个框框里面把它发挥到最大。编舞最难的是找到这个限制。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就总想做,越做越大,比如《红楼梦》,对我们来讲就感觉过于庞大,或者《九歌》,有很大的布景。这几年,舞台上的东西都非常精简,连舞台上的声音也非常精简,最后一切精简完了之后,舞台上浮现的就是舞者。你就看到演员了,看到他的呼吸。如果被一大堆的服装、故事包裹起来,舞者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舞者就要去演一个角色,为角色服务。
这些年,我作为一个编舞的人,最大的挑战和光荣就是帮助舞者。舞者是对动作非常饥渴的动物。我就是想办法喂饱他们。《行草》里还算是比较“多”了,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字,后来的《狂草》就越来越少。我有一个舞叫做《白》,什么都没有,就是白,舞台上就是白的,天空是白的。
B:你当年和刚刚出道的叶锦添合作舞台剧,你把他的方案抛在一边,把舞者全都扒光,让他们穿着非常少的衣服在台上起舞。这就可以看出你的减法思路。
L:是。因为我的确很喜欢把他们剥光,那样太好看了。他们的身材很好看。当你把他的衣服减到最少的时候,连他的呼吸,局部的身体,特别是腹部的动作,都可以传达出不同的讯息。宽袖大袍看到的是一个形象,不是身体。叶锦添老是喜欢讲这个故事,我真想杀了他。因为当初是他要给我们做服装,但是他去大陆拍片,老不回来。我只好自己动手,就用最简单的办法。结果他回来就只做了两件衣服。
B:你从加法到减法、从激烈到平静的过程,我觉得也是你个人的修行过程,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这些改变是怎样完成的?
L:我想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我希望的人生是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当然也不是故意地追求不一样。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要外扬,那时动作多得不得了,热烈得不得了,觉得只有这样才过瘾。“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没事找事来发挥、夸张。为什么要夸张?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事情可以说。年纪大了以后,经历多了,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的,最好的状况就是简单。当什么都没说的时候,大家可以意会、揣摩、诠释的空间就大了。因此这是舞蹈很重要的一个天性,文字说得清楚的事情也就不需要舞了。
我不愿意说舞蹈抽象,它不是标题式的,因为身体不抽象,身体很具象。所以我觉得这跟生命是有关系,和佛家的某些感觉也有关系。我信佛,虽然不太规矩,不是天天在做功课。所以我现在过得比较好,年轻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太多,每一样事情都强求。去了印度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活着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能做多少就尽量去做,成败、结果不重要。结果心宽了、体胖了,就自由多了,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年纪大了以后才慢慢地有了一些好的作品。
B:你现在还是每年都会去印度吗?
L:我下个月去第十次。
B:你还会到菩提树下坐一会儿吗?
L:我就是专门去那里。我们现在在台北演三部曲,演三个礼拜,20 号演完,21号乘飞机,我们第一次去泰国曼谷演,演完以后去澳洲演,然后到伦敦演。从伦敦回来的路上,我就到印度去了。我现在没有办法每年去印度,上次去,几乎是三四年前了。我很开心,我已经开始有点兴奋起来,一想到要去,我就开始过得好一点,很开心。
B:书法和舞蹈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是知名作家。舞蹈和写作,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L:很不一样。因为写书,隔了很多年,还能收到版税。而舞蹈,一天到晚在找钱,因为要养人。写作是个人行为,舞蹈都是跟别人的合作。而且舞蹈有一个很要命的事情—书写完了放在书架上,隔了几十年还在这儿—可是舞蹈老是要演,老是要面对旧作品。另外,书印好了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改不了,但舞蹈还是天天可以改,当然也很烦。唯一相同的就是创作的心思、幻想、创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企图解决困难的快乐、痛苦和狂欢。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