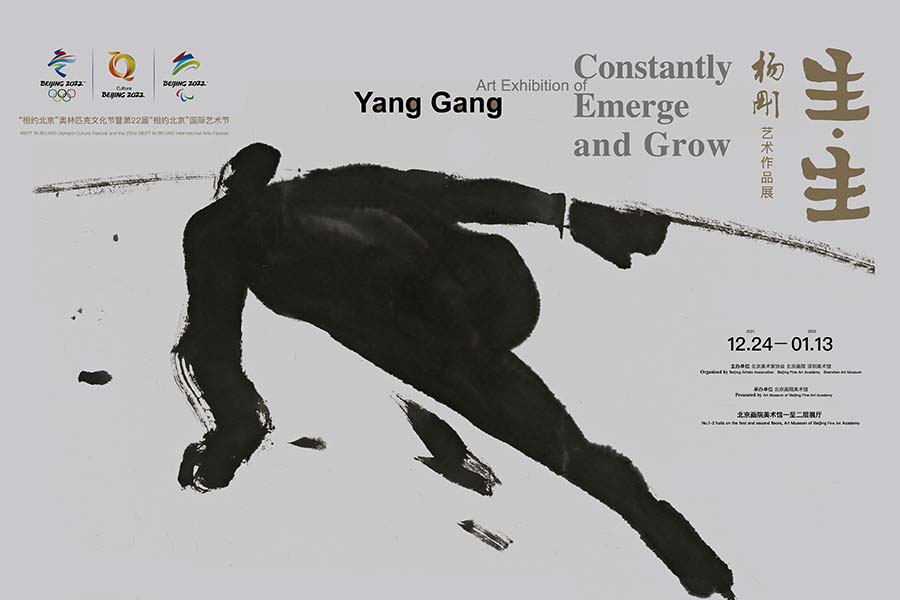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掀起。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古籍的保护工作方兴未艾。
2007年,国家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决定对全国古籍及其保护情况进行全面的普查、建立珍贵古籍名录、加强古籍书库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修复、培养高水平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国的古籍得到全面保护。笔者常年从事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亦曾经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工作,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深感宗教界应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参与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工作。
一、宗教古籍的历史
什么叫宗教古籍?按照我国图书馆界目前通行的定义,书写或印刷于清朝末年,亦即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书籍,统称为“古籍”。按照这一定义,举凡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中华各民族用各种文字书写或印刷的,内容与宗教相关的古籍,均为中华宗教古籍。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传统。从古至今,中华大地流传过种种宗教。其中,有传统的道教与民间信仰,有从西域传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乃至最终成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有从域外传入但最终消亡的摩尼教、祆教,而同样从域外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则至今仍影响着广大的群众。古代,我们的祖先在创造与吸收多种宗教的同时,翻译、编纂了浩如烟海、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宗教古籍。宗教古籍的文种非常丰富,有汉文、藏文、蒙文、满文、傣文、回鹘文、粟特文、和田文、佉卢文、龟兹文、焉耆文、东巴文及其他各种文字。这些文字有的依然流通,有的已经不甚流通或已经消亡。形式主要有写本、刻本,此外还有刺绣本、金银铜鍱、拓片等。装帧形式则有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粘叶装、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线装及其他方式。宗教古籍记录了各宗教的理论教义、修持方法、戒律规范、法事仪轨、历史方志,是各宗教学习本宗教教义、教史,展开宗教活动的基本依据。因此,宗教古籍既是各宗教立教、传教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也是学术界对中国宗教进行研究的珍贵资料。
古代,我国的宗教典籍曾十分流行。以佛教为例,由于佛教把佛典,特别是佛教大藏经视为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主张抄写、印刷、念诵、流通、保护佛典有着莫大的功德,所以对典籍特别重视。以致在我国形成历朝历代都要刊刻佛教大藏经这样一种世代相续的文化传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五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全唐文》卷七二一,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在谈及唐代佛教典籍流传情况时称:“历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兰台秘阁,而不系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惟王公达于众庶,靡不求之,以至徼福佑,防患难。严之堂室,载之舟车,此其所以浩瀚于九流也。”就道教典籍而言,《隋书·经籍志》卷三五著录道经1216卷。到了唐代,道教在李唐王朝的扶持下更加兴盛,开元年间编纂的道藏《三洞琼纲》规模达3744卷。
遗憾的是,其后我国的宗教古籍大多亡佚,百不存一。古代的佛教写经,如不计敦煌藏经洞及近代各地考古所出,真正属于传世本的,稀如凤毛麟角,只有屈指可数的若干件。至于刻本佛典,虽然早在唐代,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已经出现,晚唐五代的雕版印刷术已经非常成熟,刊印了许多佛教典籍。但我们现在能够确证为北宋以前的刻本佛经,不过十件上下。至于刻本大藏经,我国仅宋元时期就曾雕印过10余种。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是北宋《开宝藏》,其版片总计达16万多块,收经多达6000至7000卷。北宋王朝曾将该藏分赐辽、西夏、敦煌、吐鲁番、高丽、日本、越南及北宋境内诸多名山大刹,当时的流通量非常巨大。但最近我们在世界范围寻觅,真正能够落实的只有区区12卷,其中首尾完整的只有3卷。目前国内保存较多的宋元刻本大藏经是南宋刊刻、元代补雕的《碛砂藏》与元刻《普宁藏》。其中《碛砂藏》虽然大体完整,但实际均为明代印本。《普宁藏》虽在山西、江苏、云南存有多部,但每部均不完整。其中最多的一部,只占全藏的三分之一左右。珍贵的佛教古籍凋零如此,思之令人黯然。就道教而言,虽然唐宋元三朝都曾编纂道藏,但均亡佚无存。现存完整的道藏乃明朝正统年间所编。追究我国宗教古籍亡佚的原因,人们经常提到的战争、动乱、水、火等天灾人祸。笔者认为,天灾人祸的确是我国古籍受到巨大损失的重要原因。但具体到宗教古籍,则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尚未被人们提及。
(一)四部书范式的影响
古代,中国文化始终以儒家为主干。儒家主要依据经史子集四部书张本立说。其中经、史两部,是儒家立身、治国之依据与镜鉴;子部收入诸家杂著,其中如医、农、兵、天文等类,为实用类书籍;集部主要收入儒家文人的诗文集,诗文虽属小道,亦可陶性怡情。四部书体系充分体现了儒家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理念。虽然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为主干、佛道为羽翼的局面,儒释道三家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之鼎。但儒家四部书范式并不平等看待释、道两教,仅把他们纳入子部,与医、农、兵、阴阳家等并列,设立“释家类”、“道家类”。且“释家类”、“道家类”不收佛教的大藏经与道教的道藏,所著录的佛、道书籍,往往因编撰者个人兴趣与当时的条件,具有很大随意性。因此,历代《经籍志》、《艺文志》虽然收入若干佛、道典籍,但只占当时流传的佛道典籍的很小一部分,不能体现那个时代佛、道典籍的真实情况。宋朝以后,儒家文化复兴,儒家知识分子牢牢把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佛道两教则日益式微。儒家文化虽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刚性僵化的一面。儒家的这种话语主导权延伸到图书领域,不仅使一千多年前产生的四部书体系绵延继续,且对释、道两家图书的排斥日益严重。如清代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对佛道著作的收录就非常单薄,受到后代陈垣等著名学者的严厉批评。
除国家的图书庋藏外,宋以后私人藏书兴起。私人藏书家大抵为儒家知识分子,藏书的著录方式均沿袭四部书体系。这样,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公私藏书的四部书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文化范式,这一文化范式逐渐浸润于全社会。对这个范式应如何评价,是另外的事,但这个范式对我国宗教古籍的保护,却是弊大利小,且其流弊至今犹存。
举例而言,近代以来,我国的文献目录学研究领域虽有梁启超、姚名达、王重民等先贤倡导在先,但不少论述古代文献目录学的著作,言必称四部书,对佛道两家的目录学或视而不见,或涉猎甚浅。其实,唐代佛教目录学的水平雄踞于当时我国目录学的最高峰。以至宋、元、明四部书目录学都未达到唐代佛教目录学的高度。讲文献目录学而舍弃佛道两家,未免有抱残守缺之嫌。又如,目前我国各图书馆古籍部门的藏书,均沿袭四部书体系,有的虽有略微修订,但没有大的改观。因此,当涉及古籍普查与保护的一些重大项目时,虽条文中将宗教类古籍列入,但工作中往往受四部书范式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宗教类古籍。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来参与多个古籍保护的重大项目,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
(二)各宗教自身的原因
古代,儒释道三家共同支撑中华文化之鼎,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独立编目、自成体系。《隋书·经籍志》记载,隋炀帝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收藏儒家经史子集四部书;在内道场收藏佛经、道经,并分别编撰目录;建妙楷台,收藏名家法书;建宝迹台,收藏历代古画。这可说是隋代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的基本规制。历代王朝沿革虽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别庋藏的传统不变。与中央相同,古代地方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儒家的学宫书院收藏四部书,释、道两家的寺庙宫观收藏本教典籍。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体制中,各宗教的图书,实际上主要靠各宗教自己来收藏与保护。本文前面批评四部书范式对保护宗教古籍存在消极影响,是因为四部书范式在我国图书文化中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必须对中华宗教古籍的损失亡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决不是说宗教古籍的亡佚,责任完全在四部书范式。因为归根结底,各宗教的图书主要靠各宗教自己来保护。所以,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各宗教图书保护情况的好坏,责任主要应由各宗教自己承担。
应该说明,各宗教对本宗教的图书都予以相当的关注与重视,也都会予以保护与整理。但是,毋庸讳言,不同的宗教、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同一派别的不同收藏单位对本宗教图书的重视程度不同,所采取保护措施的力度不同,最终的效果也会不同。
二、宗教古籍的现状
中华宗教古籍的现状如何?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在此就个人所知,对目前我国宗教古籍收藏、保护与整理的情况,做一些粗浅的介绍。由于笔者主要研究佛教,对其他宗教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因此,这里的介绍也以佛教为主。
(一)收藏单位及其保护
我国的宗教古籍,大体收藏在如下五个地方:
第一,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
这里主要指国家图书馆、各省级图书馆、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图书馆。此外,不少地、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某些出版社的图书馆,均收藏有宗教古籍。总的来讲,图书馆的级别越高、历史越悠久,收藏宗教古籍的数量可能就越多。
就保管条件来说,国家级、省级图书馆基本都有恒温恒湿的古籍善本专用书库,宗教古籍与其他古籍一起得到很好的保护。但一些地、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保管条件则相对较差。我曾到某县级文化馆考察,那里收藏了一部珍贵的《嘉兴藏》后期印本,存放在一间狭小的平房中。保管者除了紧闭封锁以求不丢失外,无力作进一步的养护。当我进入那间多年未曾有人进入的狭小房间,看见到处堆积着厚厚的灰尘,心中感慨,实难自已。后来曾动员南方某佛教寺院出资以改善收藏条件,最终未果,至今引为遗憾。多年未去,不知目前情况如何。
就古籍保护而言,国家图书馆有古籍修复机构。如上世纪50-60年代,国家图书馆修复了著名的《赵城金藏》。90年代又配合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目与出版,对馆藏敦煌遗书做了大规模的修复。有些省级图书馆也有专业人员从事古籍,包括宗教古籍的修复。但大多数图书馆缺乏图书修复的专业人才,很多残破古籍未能得到有效养护。不过,2007年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把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想必将来情况会大为改观。
第二,各地的博物馆、文博馆。
从国家博物馆到各省级博物馆,乃至地、市、县级博物馆、文博馆等地都藏有宗教古籍。在论及宗教古籍时,这一部分藏品经常被人们忽略。实际上,这些单位收藏的宗教古籍往往品质很高。
博物馆、文博馆中宗教古籍的保管、保护现状,与图书馆情况差不多,即级别越高的单位,条件越好;级别较低的单位,条件则相对较差。我曾经考察某县级单位,他们的收藏品属于国宝级文物。但是,该单位不但没有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连必要的安全措施也没有完全到位。以致为了保证藏品的安全,多年来,馆长、副馆长每晚轮流值班看守。我很为他们的这种负责精神所感动,也为如此珍贵的宗教古籍未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而悲哀。他们的收藏品,有的已经部分碳化,无法触动,急需养护。我曾经专门向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汇报。先生指示,国家图书馆可以免费为之修复。但由于种种原因,修复工作至今没有能够进行,言之令人痛心。第三,各地的档案馆。
这又是一个一般人不甚关注的宗教古籍收藏单位。其实,在各级各类的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宗教有关,或者本身就是宗教古籍。
按照档案法,目前很多档案资料已经超过保密期,可以向研究人员及社会公众开放。但由于研究者不知道档案馆也有宗教古籍,所以这一部分资料还没有完全进入相关人员的视野,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第四,各宗教团体。
各宗教团体都收藏宗教图书,其中很多团体程度不等地收藏有宗教古籍。
一般来说,各宗教团体均将现代图书与宗教古籍分别存放。比如佛教寺院,将古籍,特别是大藏经供养在藏经楼,而将一般图书存放在图书馆、阅览室。但也有相互混杂的情况,即藏经楼供养的,既有古本大藏经、其他佛教古籍,也有现代出版大藏经乃至其他现代书籍。而图书馆中,有时也存放少量的古籍。
就保管条件而言,随着这些年寺院建设的大发展,很多新建寺院修建了宏伟、庄严的藏经楼。建筑虽然宏大,但除了少数寺院外,大多数寺院的藏经楼都没有考虑保存古籍所需的恒温恒湿等条件。至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寺院,藏经楼依然是多年前的老建筑,有的经过维修,有的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楼板吱吱作响,更不用说恒温恒湿之类的保管条件。更有甚者,藏经楼虽然供养着多部藏经,却常年闭锁。名义有人看管,实际无人照料。灰积尘蒙,听之任之。由于没有专业修复人才,寺院无法开展宗教古籍的修复工作。我们自然不应以此苛责寺院。但是,确有不少寺院缺乏古籍保护意识,对所藏古籍缺乏关心。南方某寺,藏品长期无人过问,据说颇有损坏、丢失等情况。直到后来中国佛学院毕业的某年轻僧人担任监院,才予以编目、保护。北方某寺收藏大批古籍,其中不少古籍扃锁多年,从不检视,亦不知是否有虫蛀鼠啮。甚至有的寺院见有些古籍虫蛀、霉烂,干脆一火了之。总之,除了少数寺院外,大部分佛教寺院古籍保管、保护的情况,令人很不乐观。
第五,私人收藏。
我国民间从来有收藏的传统,很多宗教古籍收藏在私人手中。从这些年诸多拍卖公司及网上古籍拍卖的情况看,私人收藏的宗教古籍数量颇为可观,这是我们从事宗教古籍保护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提到私人收藏,我想特别提出关于佛教忏仪文献的收藏问题。作为宗教仪轨,忏仪是佛教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下,以大规模忏仪为代表的信仰层面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之一,对佛教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佛教大藏经的发展已经滞后于佛教的发展,大量忏仪文献未能收入大藏经。它们流传于民间,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不少忏仪古籍因此亡佚。忏仪文献的这种存在状态,对我们研究宋以下佛教造成极大的障碍。多年来,笔者始终关注这一问题,并与同事一起收集了民间流传的忏仪文献数百种,其中不少均为古籍,有些甚至可以定为善本。其实,我们收集到的,只是民间传本中很小的一部分。希望更多的人士能对这些民间传本有所关注,注意收集。
私人收藏的保管、保护情况,因人而异,很难一概而论。
宗教古籍是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不少为孤本,承载的信息是唯一的;不少为善本,本身又是珍贵的文物。这些古籍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对宗教古籍的保护迫在眉睫,应该引起各地宗教事务部门、宗教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二)宗教古籍的整理
下面分目录编纂与文献整理两个方面谈谈当前宗教古籍的整理。
第一,目录编纂。
近些年来,我国在宗教古籍的编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就图书馆而言,作为全国古籍整理项目之一的《全国古籍总目》已经完成,其中《子部·释家类》由南京图书馆善本部负责编纂,这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图书馆所藏佛教古籍的联合目录。遗憾的是该目录仅涵盖我国几大主要图书馆的藏品,没有包括所有的省级图书馆,更不要说地、市、县图书馆。就寺院而言,苏州戒幢律寺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编纂了寺藏古籍的目录。四川文殊院近年也将寺藏古籍编纂了目录,并计划继续将四川其他寺院的古籍也逐一编目。就专题目录而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也即将完成。但是,也应该指出,与浩如烟海的中华宗教古籍相比,上述工作还是非常不够的。本文上面从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华宗教古籍的收藏,下面谈谈它们的编目。
我国不少图书馆已经将自己馆藏的古籍(包括宗教古籍)编成目录,公开出版。但也有不少单位的古籍目录中不包括所藏的宗教古籍,或不包括所藏的全部宗教古籍。据我了解,有的图书馆收藏的宗教古籍数量相当大,但因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至今尚未编目。
我国的博物馆一般不公布藏品目录。所以,对博物馆收藏的宗教古籍,除非得到相关博物馆的允诺及大力配合,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否则难以了解其实际收藏情况。
就档案馆而言,除已经整理出版的专题档案外,档案资料一般不公布目录。保存在档案馆中的宗教古籍的专题目录,至今无人编纂。除了少数寺院外,绝大多数寺院的古籍,均无目录。至于个人的收藏品,自然更无目录问世。由此可见,宗教古籍的目录基础非常薄弱。
第二,文献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宗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此特别应该提到汉文、藏文、傣文三大语系佛教大藏经的整理。由任继愈先生主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历时13年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总107册。该藏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将历代大藏经中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均皆收入,并用八种有代表性的藏经进行校勘,成为当代一部重要的汉文大藏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主持,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总232卷,是第一部现代化的藏文大藏经。由中国贝叶经全集编辑委员会主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贝叶经全集》,全100册,该书的傣文佛典逐段均有原书影印、电脑转写、国际音标、汉文翻译等四个部分,每部典籍并附汉文翻译全文及新傣文全文,是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史上的创新。上述三大语系大藏经的整理出版,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古籍整理工作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此外,近年还出版了《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共130册,涵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民间信仰等各宗教的典籍,其中包括不少宗教古籍。中国国家图书馆则将所藏敦煌遗书全部影印出版,全书约160册,已经出版133册。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对宗教典籍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段时间以来,影印宗教古籍与佛教大藏经成为出版流通宗教典籍的重要方式。应该指出,影印古籍虽然部分满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但有些质量较差,难以阅读;有些名不符实,有欺世盗名之嫌。凡此种种,值得我们重视并在将来的工作中改进。
宗教古籍不仅具有供养功能,还是宗教界人士及研究人员学习研究宗教的重要资料。单纯的影印,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对宗教古籍进行深度加工,即校勘、标点、撰写提要等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以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佛教典籍丛刊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笔者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致力于整理发表敦煌遗书及民间散落的历代大藏经未收佛教文献,陈士强先生多年来在佛典提要的撰写方面用力甚勤。近年,一些佛教寺院开始致力于佛教古籍整理,如鼓山涌泉寺与学术界合作,将寺藏古籍(版片)中的重要文献校勘标点,嵩山少林寺也将寺院中的石刻碑铭录文整理。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文献整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古籍的电子化。目前,宗教古籍电子化的工作也正在蓬勃开展,已经取得良好的成绩。
与我们面临的任务相比,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可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
三、对宗教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展望
我国是汉传、藏传佛教的故乡,也是南传佛教的重要流传区域,是三大语系佛教并存的唯一国家。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迟早会成为世界佛教研究的高潮。就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的其他宗教而言,同样会遇到与世界同行进行宗教交流、对话与研究的高潮。为了迎接这一高潮,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
为了真正有效地对宗教古籍进行保护与整理,当前需要进行三项工作:
(一)要普及宗教古籍意识
宗教古籍保护、整理工作能否顺利展开,与有关人士的古籍意识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在相关人员中大力普及宗教古籍知识,培育与提高宗教古籍意识,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宗教古籍的价值,主动自觉地投入到宗教古籍的保护、整理工作中。
我认为,提高宗教古籍意识,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认识到宗教古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们既是宗教界的重要财富,也是全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任何人,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毁伤的权力。保存尚好的古籍自然应当精心爱惜,已经残破的古籍更应该努力保护。再也不要发生将残破古籍一火了之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对古籍如果仅仅是扃锁起来,束之高阁,不准阅览,并不是真正的保护。那样做,有古籍等于无古籍,使活宝变成死宝。因此,任何古籍收藏单位,都应该促成古籍的合理使用,让它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促进各宗教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如何正确处理使用与保护这一对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
(二)组织力量,进行宗教古籍普查
我国现存宗教古籍到底有多少?分布情况如何?不同古籍的保存状态如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宗教古籍保护与整理时必须首先落实的问题。有了符合实际的调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整理方案。目前,国家正在进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的古籍普查,也包括宗教古籍的普查。遗憾的是,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除了少数单位外,宗教界对国家这次的普查工作普遍表现出热情不高,参与度较小。我们希望宗教界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一利己利国的活动中。我们更希望各宗教古籍收藏单位,能够将本单位收藏的古籍编纂为详尽的目录,最终争取编撰成全国联合目录,为进一步做好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宗教古籍整理
目前,宗教古籍整理的势头很好,但问题不少、困难很大。就编印大藏经而言,不少单位正在从事这一工作,有的单位正在计划推出新的大藏经编印工程。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单位编印的大藏经定位不清,大量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有限,是否有必要去做那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值得有关人士深思。
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建设的新时代,时代要求我们拿出文化精品。古籍整理工作,本来就容不得半点浮躁与虚夸。我们只有沉潜笃实、精益求精地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真正打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协调相关宗教单位与学术力量,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分清主次,区别重点,分批分期,逐步展开,并充分利用电子化手段,将宗教古籍整理的工作提升到新的层次,尽可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文化财富。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