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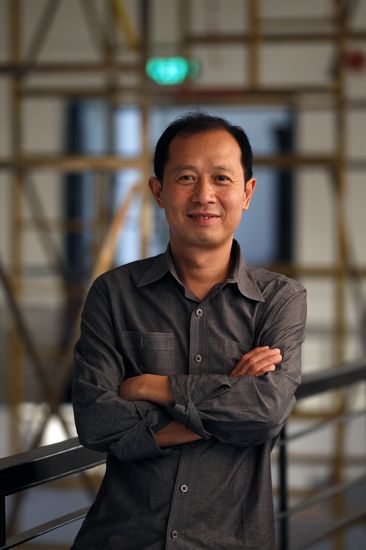
独立策展人侯瀚如 许海峰 图
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华裔策展人侯瀚如有十余年的国际策展经历,从1994年芬兰的“走出中心”,1997年的“运动中的城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这十余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侯瀚如是没有一个“单位”支付给他固定工资的,侯瀚如说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策展人。
艺术评论:如何能让艺术家在策展人所界定的主题当中获得更多的自由,或者是艺术家的作品拓展了你的主题?
侯瀚如:对,当然我觉得艺术家的自由是首先要考虑的,我从来都觉得一个展览如果把艺术家的作品作为一个主题的插图,那是最糟糕的,而实际上你提出的这个所谓概念或者我一般都叫conceptaul
framework概念架构,这个东西只是给予艺术家的创作一个定位,但是他本身的概念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东西,我只是把这个相对比较独立的东西放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定位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因为和这个定位发生关系同时也令观众可以参与进来,这样的话会形成阅读上的开放性,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提到的“作者之死”,这种说法、关系我觉得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很简单的、封闭的、固定的,它仍然是在不断地被阐释当中,所以我们做展览的本身就是把阐释的过程加以更加有意思的强化。
艺术评论:策展人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几年前连策展人的概念都没有,在1997年的时候做策展人和现在做策展人感觉上有什么不一样?
侯瀚如:从根本上来说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种的跟更加具体的环境打交道的一些方式,而十几年前,我更强调是自我组织的、即兴的、临时的策略,来把一些作品的独特方面和能量表达出来。但是今天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当代艺术变成了越来越官方化,我的意思不是说变成官方的东西,而是正式化、体制化,就是说做艺术有了套路了。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艺术变成了一个正正经经的市场上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市场化、体制化的背景,还能够使得艺术它本身超越这样一种限制,而保持它在精神上面、智力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这就是说现实比十几年前更加具有挑战性,策划人面对的精神上的要求更高。十几年前实际上更自由,
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也非常不一样。现在艺术家的素养,比十几年前高很多很多,展览多了很多,博物馆多了很多,
杂志什么的也多了很多,各方面都多了很多。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第一就是作品的质量普遍在提高,但同时它越来越失去尖锐性,越来越失去这种个别、金鸡独立的、突出的性格。这是一个矛盾。
艺术评论:这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吗?
侯瀚如:当然是。中国基本上就是更加有效率,但是更加临时的,质量更低的国际化倾向的一个版本,就好像中国的生活非常昂贵,但是都是一种非常廉价的、没有质量的昂贵。这对于我们策展人来说也是挑战,策展人本身,在十几年以前并不是一个主导,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行当,有学可上,有书可看,这样的话变成了条条框框很多,而且我们现在都在教学生怎么去做一些好的展览,好像好的展览是可以很明确地去描述的。但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觉得越是这样明确的话就越是要想办法把它打破。
艺术评论: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展览才是一个好展览?
侯瀚如:如果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能做得好的展览就是,很认真、很准确地把作品的完整性表达出来的一个展览,把作品的真正的内容和学术的艺术纯粹性,它的力度表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谁也不能说画抽象画就比做录像的低级,但是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但你做一个展览的话,就算你做一个古董的展览,你还得把古董里面所含有的历史背景、作品在历史背景里的独特性能够用一种很敏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把作品像一个活着的生命一样,呈现在别人面前。作品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必须是活的,这个不光是针对中国了,对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教学生怎么去做好的展览,这是把展览作为一个死的东西去看,而没有办法使别人感受到这些东西是活的,它背后的艺术家,它背后的生命。有一天这个作品因为物质的原因,可能会死掉,会消失掉。做展览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的生命在一个空间里面表达出来,就是要把作品活生生地展现出来。
为什么我们需要展览?为什么艺术家的东西可以上网 随便就能看到很多东西?为什么我还要去看展览?因为它是全身心的一种感受。
艺术评论:策展人还身兼批评家的角色。
侯瀚如:策展人不是身兼,他就是批评家。如果策展人不是批评家、不是一个艺术史家的话,他就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他跟那个美术馆里面看门的没有任何区别。
艺术评论:策展人身兼了一个发掘人、批评家的角色,甚至有些策展人还会在当中参与一些画廊、画作的经营,参与买卖。
侯瀚如:这个和我没什么关系,这个是别人要干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做事都非常单纯,我也要做其他很多各种各样事务性的事情,我也要去找钱、做很多社会关系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也在管两个部门,我的学校里面的两个部门,那么就有很多日常的、行政的东西,每做一个展览都有很多行政性的事务非常多,那么这个东西你不可能纯粹是一种文化上的,艺术上的东西,虽然我们花很多开支,70%~80%以上的时间去做很多很零碎的事情、办公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原则,就是我的工作,我自己的工作绝对不会是一种盈利的目的,当然不可避免地谁都要挣钱、吃饭交房租的。
艺术评论:确实不太看到过你有商业文章。
侯瀚如:这是我的原则,从来不做。我可以给艺术家的画册写文章,因为他们是我喜欢的艺术家。但写这个文章有很微妙的一点——因为你给一个画册写文章,往往都只能够写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为什么接受写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好的,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才会去写。我不会随便接受一个任务,因为人家给我很多钱我就去写一篇应景的文章,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和广告完全不一样,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很像写广告,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
艺术评论:你策划过很多国际展览,比如伊斯坦布尔,也做过广州双年展和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你觉得国际策展和国内策展的经历有什么不一样吗?
侯瀚如:国内也有一些相当不错的策展人,当然从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像我们大家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十几年来艺术都变成了一个主流的一种,社会主流的一种高尚活动,有的时候甚至成了一种高级娱乐,这个时候其实就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提出了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你不可能离开现行制度,因为它就像空气一样的围绕着你。要么你就彻底不要做展览,但是如果你继续要做的话,必须要跟各种各样的市场、机构打交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还有和自己合作的艺术家和机构,我们干这个事情是为什么。
可能在美国的策展人更有一种知识分子对待艺术的态度。但是他们中的多数要不就是学院派,要不就是在非营利机构工作,比较顺从、规规矩矩做事情。我觉得中国好像这两方面都没有。就是说学院派也好、很规矩的策展人、知识分子的策展人都没有,这些成分都很少,而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回答一个马上就要实现的任务,很事务性。
国内的策展人很少有一个对艺术的个人信念,就是说“我相信艺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有这样信念搞艺术才是对的。国内的一些策展人可以把一些商业画家和严肃艺术家如黄永砯等放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对我来说黄永砯是艺术家,那些商业画家就不是艺术家。
在国内做一个艺术家好像很容易,但不少人没有自己的艺术信念,没有自己的艺术价值的标准,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很多作品,但是这个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不是艺术。
艺术评论:那你的艺术信念是什么?
侯瀚如: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它用一种非常个人的、独特的语言,但是同时又能说出一些对于我们的生活、内心生存状态的一种有批判性的阅读,这个对我来说是艺术的作用。然后从本体上来说可能它是给我们带来看世界的另外一种方式并付诸实践。你的做人的方式可能会很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涉及到,就是说每个人的独立的、知性的一种历程,这是一个像生命一样的东西,必须要有一种很特殊的生命形式,这个对我来说才叫艺术。
艺术评论:在国际策展上,你不把意识形态作为前提而跟当地的语境发生关系,那么国内的策展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妥协?
侯瀚如:应该没有吧,我想我不能做的我就不做。原因是,第一,可能邀请我做这个事情的人,他的目的和我的目的很不一样,不一样到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当然每个人要组织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目的可能和你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达成一种共识、可以合作的可能性;第二个,他对这个事情的期待和我对这个事情的期待是不同的,这个所涉及的道理还是要回到刚才关于艺术的信念的问题上去说,他想要的东西和我相信的东西是完全两码事,那么你再多的钱、再多的空间、再好的条件给我,对我来说我都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做不好的,我不可能在一个做不好的事情上面签字。就是说如果是我不想做的,我却做了,回家会睡不着觉。
艺术评论:你那么多的策展经历中有什么不可改变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坚定的立场?
侯瀚如:我想有两个原则,第一,我的这种精神上的和立场上的自由不能失去,第二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自由不能因为参与了什么展览而失去,这是我要尽我所有能力去保护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做不到,比如说艺术家作品开幕之前还没有装好,那我绝对不能接受这个展览开幕。
艺术评论:那么如果说展览现场装好以后,有当地政府或者有关机构要求这幅作品撤下来,你会照办吗?
侯瀚如:这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选择,那么第一你首先要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做什么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是很无谓的一种挑衅。它可能会变得很廉价,那么这个事情就算做出来也没什么意思。往往就是所谓被检查掉的东西,很多这样的东西,是很廉价的一种对抗,这个是没有意思的,包括有些人,不想点名嘛,弄不好变成国际明星这种,很没劲。这个对我来说和艺术没有什么关系。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批评家,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所以你才会去做这个展览,做这个很自然的、很廉价的挑衅可能不太会存在于你的展览里面,但是如果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选择要不就是机构让步,要不我就辞职,我就不开这个展览了。
艺术评论:但是也不跟他们妥协?
侯瀚如:那是肯定的。
艺术评论:你的策展经历中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侯瀚如:几乎没有,因为可能我每做一个事情时,我都在想它在某一个领域、语境里面的合适性,而且就是说它长远所带来的,比如说2000年我做上海双年展的时候,当然我也很想一步就达到所有的目的,给所有的艺术家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是不太可能,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很站得住脚的、示范性的东西,然后把这个形式慢慢形成以后。那今天,十年过去了,艺术家势必会获得更大的自由,我想这是肯定是的。那么今天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今天的课题就是“廉价的挑衅”。面对现实,你要有一个想好的底线,然后才去做,做的话,你不要期望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你要看到你做的事情的意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十年、八年的变化,所以你要做一个铺垫的工作。
艺术评论:所以展览实现的意义大过一切?
侯瀚如:展览的实现有意义,但是绝对不能够失去它的批判精神,展览的批判精神可能并不是很简单就像喊口号式的。
你仔细想一想2000年上海双年展里面有一些政治上非常不容易被官方接受的东西,但是当时它可以这样过去,这个展览可以很顺利地完成,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作品本身。它的这种力量并不就是仅仅回答你当时当地的一个几乎很gossip一样的话题的,像很低级的政治对抗的话题,而是更多的是从事情整体的命运,它的历史,来发掘到它的政治的含义。这个东西它很强烈,同时它又不需要用很多碰撞来表达它自己。比如说黄永砯的作品《银行的沙/沙的银行》,把外滩的汇丰银行的那个楼用沙子按比例复制了一遍。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批判性的作品,对于上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但是它同时又涉及到不光是中国和上海,而且是全世界的这个从殖民主义过来的经济体系,到今天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追求的某一种荒谬的地方,实际上它都含在里面了,所以它这种批判性这是一种很广义上的批判性,是最有力量的。对于我来说,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种作品,绝对不可能对那种很傻的、口号式的把两个毛泽东的头像放上去的,这种我不感兴趣,这对我来说这根本就不是艺术。
艺术评论:你是觉得符号太简单化?
侯瀚如:这方面做得好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引起太多的被检查的可能性,如果这样还被检查的话,我很佩服这个检查官,他的水平太好了。我也相信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但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不断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变化的过程,所以你怎么把握这个过程,你没有绝对的自由,你不能够说因为我是艺术家所以我就有绝对的自由,你也是个人,你也在这个地方,有些事情是有界限的,比如我们绝对不能够支持种族主义、支持法西斯和各种强权。
艺术评论:西方其实也是有界限的。
侯瀚如:当然有界限,就是说,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概念、价值观念的问题,这个有体现,所以你不能为挑衅而挑衅。确实你也要从很多面的、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你在伊拉克,或者在沙特阿拉伯,你说伊斯兰那里不好,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伊斯兰它首先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广为社会认同的信仰体系。而且你必须要尊重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你必须用理性来面对它。
比如说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信仰,你看宗教自由这个在历史的过程中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针对某一种宗教的另外一种信仰,所以现代历史的过程本身也包含了很多、很聪明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关系,
包括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的问题。
艺术评论:他们也许只是迷恋这种捍卫的感觉。
侯瀚如:很多激进动物保护主义者,宗教极端主义者去时不时会抗议一些艺术作品,但一般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些艺术作品,他们只是道听途说,听到别人说这个戏剧里面好像有反对基督的,他们就去,那前一阵子在巴黎就是这样,后面有很多政治的操作,但是你去采访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对到底作品在讲什么一无所知,他只是听说它侮辱了基督教,一般来说就是这样。
艺术评论:就好像对帕慕克的反对一样,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帕慕克的书。
侯瀚如:所以我们的判断必须依靠理性。用理性的方式弄清楚你为什么反对,我为什么反对,我为什么支持,那么这个时候对话是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就会拒绝对话,因为忽然间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非理性的。
艺术评论:在2000年做上海双年展的时候,你当时感慨万千,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
侯瀚如:当时确实我想的很多的一点,是刚才我提到的,在当时做上海双年展是很特殊的,在2000年的时候,我是想后面十年对于中国的发展,能够提供怎样的一种前景,我们做的事情好像铺路的第一块基石,这种感觉还是很强烈的,当然这种强烈也来源于我们都知道在这之前多么不容易,确实那个时候我们经历过80年代、90年代的,这种不容易当然就是说……
艺术评论:这种不容易是来自什么地方?
侯瀚如:其实当时当代艺术基本上都是地下活动,基本上都要躲起来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做艺术家确实是需要极其坚强的内心,而且我觉得当时的艺术家都是处于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因为它们在一种很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是在没有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做作品,他们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很难实现,而且如果能实现的话都是匆匆忙忙为了什么事情突然间像打游击一样的完成,那样他永远都做不出来一些很重要的作品,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完整的条件和时间,这个是当时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以前,中国绝大部分的当代艺术家都是为当时刚刚出现的国际市场去做作品,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任何条件去靠艺术生存,而且甚至连展出都很困难。
艺术评论:是不是1992年到1993年最困难?
侯瀚如:对,那个时候也很困难,一直到2000年之前,实际上相对来说都不容易。同时来说艺术家、策展人都相当的临时性,他们能做成一个展览就走。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谁说我昨天找到了一点钱,今天想一想,明天展览就开幕了,都是这样的。
艺术评论:当时的作品是怎么来的?
侯瀚如:作品就临时赶啊,我可能是夸张了一点,可能只有一个星期去组织整个展览,所有的作品都显得非常的临时性、没有质量,它只能有点灵机一动的,绝对做不出来一种很完整的东西。
我当时有一种考虑就是上海双年展能够开成的话,其中的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能够为创作条件的正常化提供一种开端,所以筹备的过程很关注于如何去让艺术机构和文化官僚接受当代艺术,更重要的是还要获得观众和媒体的支持。这样艺术家的创作条件会正常些,
可能做出有深度的作品来。要达到目的就要费很大的劲,所有的感受加在一起就让人很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