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书为桥连通世界,以文为媒共话文明

[快讯]以书为桥连通世界,以文为媒共话文明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9/24/20259241758699410175_336.mp4
[热点]绿水青山 艺术画卷——文化唤醒中国乡村活力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8/19/20258191755566615832_336.mp4
[展事]假期如何“有文化的”消暑? “山水有清音”将徽派文化带入北京
[展事]假期如何“有文化的”消暑? “山水有清音”将徽派文化带入北京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8/4/2025841754296620649_335.mp4
[展事]中国观众最熟知却鲜见原作的艺术大师——列宾来了!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7/23/20257231753241518685_336.mp4
[动态]中国外文局举办“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文化沙龙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6/12/20256121749689687510_336.mp4
[展事]写照自然,而留痕于心——罗尔纯、戴士和油画作品展艺冠空间开幕
[展事]写照自然,而留痕于心——罗尔纯、戴士和油画作品展艺冠空间开幕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4/23/20254231745389645657_463.mp4
[绘画]黑沙骆“铁笔撼山岳”——李骆公艺术研究展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
[绘画]黑沙骆“铁笔撼山岳”——李骆公艺术研究展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4/12/20254121744438023804_463.mp4
[展事]笔底春风殊未老——北京画院37位老画家作品汇聚一堂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5/1/22/20251221737516225717_342.mp4
[热点]“高峰意识”潘天寿、潘公凯艺术研究展开幕 潘天寿艺术中心正式开馆
[热点]“高峰意识”潘天寿、潘公凯艺术研究展开幕 潘天寿艺术中心正式开馆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12/31/202412311735633777612_342.mp4
[展事]齐白石的艺术Plog:画画、交友、吃饭……邀你走进他的北京朋友圈
[展事]齐白石的艺术Plog:画画、交友、吃饭……邀你走进他的北京朋友圈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12/2/20241221733139338135_463.mp4
[热点]【必看】八个你不能错过“传奇之旅: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的理由
[热点]【必看】八个你不能错过“传奇之旅: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的理由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8/5/2024851722844310400_463.mp4
[展事]回首风尘,徐悲鸿、廖静文的珍贵手札里写了什么?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8/5/2024851722846813127_463.mp4
[视频]时代记艺·北京画院老艺术家推广系列——艾轩:雪域回响(上)
[视频]时代记艺·北京画院老艺术家推广系列——艾轩:雪域回响(上)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7/8/2024781720418370958_342.mp4
[视频]时代记艺·北京画院老艺术家推广系列——艾轩:雪域回响(下)
[视频]时代记艺·北京画院老艺术家推广系列——艾轩:雪域回响(下)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7/8/2024781720418534355_342.mp4
[视频]方李莉:“先锋人群”正在景德镇创造一种中国新的生活样式
[视频]方李莉:“先锋人群”正在景德镇创造一种中国新的生活样式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6/19/20246191718761285534_336.mp4
[动态]中国外文局外籍专家参访北京城市副中心活动圆满举行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6/18/20246181718691685761_336.mp4
[视频]“寻一求真——沈岩诗书画展”在福州开展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4/5/17/20245171715931130135_342.mp4
[展事]心游故土 寻源问道:“游走——刘巨德艺术作品展”在北京悦阳空间开幕
[展事]心游故土 寻源问道:“游走——刘巨德艺术作品展”在北京悦阳空间开幕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3/12/7/20231271701913238717_463.mp4
[展事]艺术家与批评家携手举办的展览——北京画院新展“点画”开幕
[展事]艺术家与批评家携手举办的展览——北京画院新展“点画”开幕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3/11/14/202311141699955264238_335.mp4
[展事]从“葵园如山”到“所念皆山”,许江二十年绘画在京展出
[展事]从“葵园如山”到“所念皆山”,许江二十年绘画在京展出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2023/11/7/20231171699325877329_335.mp4
[展事]艺术狂想:欢迎来到Mr Doodle的梦幻世界——Mr Doodle(涂鸦先生)即兴创作,点亮澳门之行
[展事]艺术狂想:欢迎来到Mr Doodle的梦幻世界——Mr Doodle(涂鸦先生)即兴创作,点亮澳门之行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9/16/20239161694795108284_463.mp4
[展事]东京富士美术馆藏56件西方人物画真迹登陆国家大剧院,件件精品,推荐打卡!
[展事]东京富士美术馆藏56件西方人物画真迹登陆国家大剧院,件件精品,推荐打卡!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8/7/2023871691392792528_336.mp4
[展事]“朱乐耕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中国式视听艺术场景诠释“在传承中创造”的精神题旨
[展事]“朱乐耕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中国式视听艺术场景诠释“在传承中创造”的精神题旨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7/19/20237191689749516555_463.mp4
[动态]纪念屈原逝世2300周年 170余位国际友人共聚汨罗体验端午文化
[动态]纪念屈原逝世2300周年 170余位国际友人共聚汨罗体验端午文化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6/27/20236271687832858014_336.mp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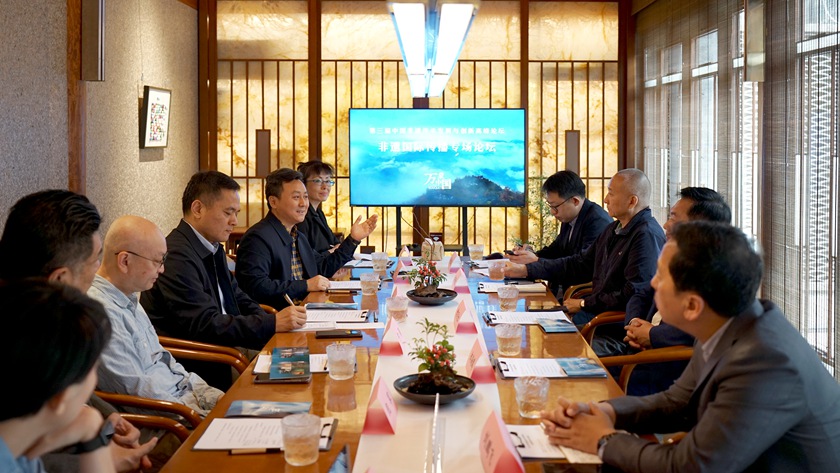
[思想]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非遗国际传播专场举行
[思想]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非遗国际传播专场举行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5/16/20235161684220129824_336.mp4
[现场]文艺复兴至当代50幅艺术大师自画像来到国博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4/27/20234271682594553447_463.mp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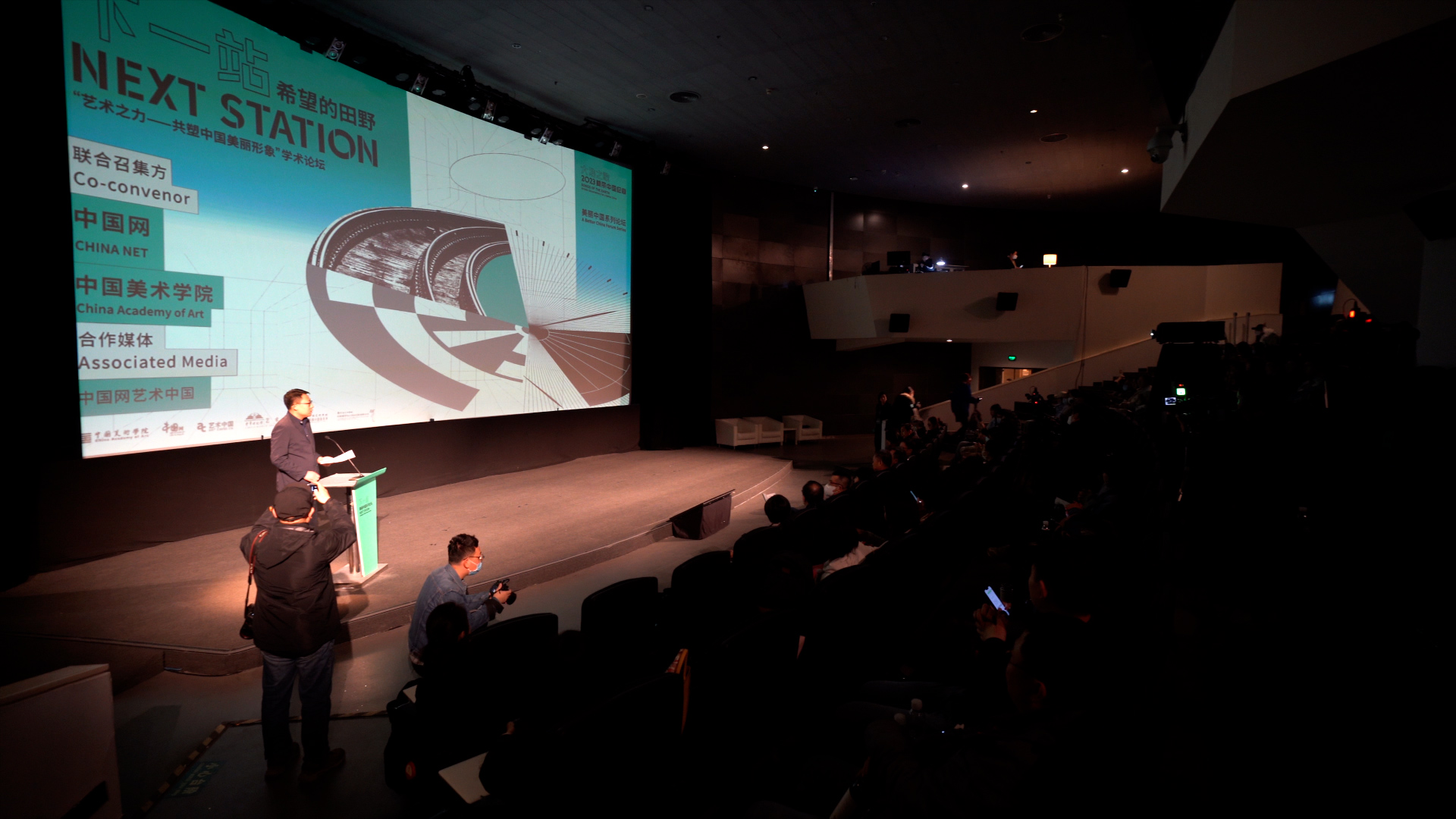
[热点]“艺术之力一一共塑中国美丽形象”学术论坛在京召开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3/21/20233211679358813977_336.mp4
[展事]百余案例谱绘华夏“大地之歌”,中国美术学院邀您共赴“美丽中国”之约
[展事]百余案例谱绘华夏“大地之歌”,中国美术学院邀您共赴“美丽中国”之约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3/9/2023391678323411628_463.mp4
[展事]炁象,在精神的空间里升腾——马路45年艺术发现之路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3/7/2023371678170450498_336.mp4
[展事]刘商英:十二年,穿越万里荒原,用身体触摸自然
http://mp42.china.com.cn/video_tide/video/2023/2/28/20232281677547000592_336.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