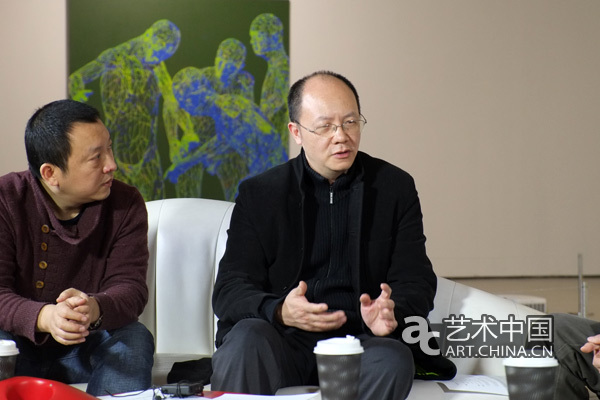
参展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缪晓春教授在发言中
许柏成:其实数字艺术脱离不开科技以及对于艺术思想内涵的表达,那三位老师怎么看数字艺术里面科技和艺术相互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
缪晓春:我觉得每个时代肯定有它崭新的技术,艺术家有这样一个责任或者义务去尝试新的技术去做他的作品,但就像你刚才说的,技术最重要的是跟思想结合起来,要反映它最原始最根本的想法,所以我也特别喜欢那种看起来技术并不是太领先,但是还是反映了很深刻的思想的东西。就像白南准做的对着电视机的一个佛,这个技术现在看来已经很简单了,但是这件作品给我的印象一直非常深刻,我一直觉得它是白南准最好的作品之一,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实际上有非常深刻的东西在里面,你可以做各种各样反复的解读。
我们用新的媒体新的技术来做这个作品,其实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一旦这个技术过时了,你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能感动观众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大浪淘沙,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后我们现在的这些技术,说起来都会是不值得一谈的东西,但是真正能够打动人的东西才是会留在艺术史上的。
张小涛:我补充一下,做新媒体、做数字艺术最怕的是炫技,你看这些孩子多半学完这个就去做商业去了,真正留下来做当代艺术的其实需要一种传统的、千年不变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灵魂。比如说影片的这种穿透力,艺术中的人性、神性、兽性等等。我做数字媒体的时候,同时对考古特别感兴趣。我做的第二个片子《迷雾》,是和重钢、重庆的城市变迁和工业现代性以及物欲是有关联的,在这个课题下我其实在用动画语言数字艺术在去围绕课题去完善。然后比如说做《萨迦》,其实是和藏传佛教有关系,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动画电影,其实和我当年的青春期和一个城市的这种90年代的巨变,中国社会家庭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创伤、社会巨变。我觉的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共性,其实你越掌握了技术,你越不应该炫技,比如我看老缪的“布鲁盖尔”和“最后审判”,其实他是从西方美术史里面来的养料,为什么用数字媒体来做这种宗教题材和美术史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变的。甚至有时候我更愿意在做数字媒体的同时看一些传统的东西,昨天晚上我还在看牧溪、法常,包括担当、八大,这些类古代的、很传统的画家,在今天你依然会很感动,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变的。
媒介永远变,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做数字媒体的一个课题、一个方法、一个系统。自己的体系、逻辑和语言有没有一个比较深的脉络,这是做数字媒体应该非常警惕的东西,否则很容易走向炫技。软件每天都在更新,就像人不可能永远漂亮,你会苍老,但苍老也可以有苍老的味道,是另外一种境界。我觉得这种怀疑和警惕,在新媒介里面是一个双刃剑的地方。今年我还报了我们学校的项目,是巴蜀石刻在意大利博物馆的一个项目,我也是借鉴了《萨迦》的元素,就是用考古学和新媒体的这种还原,数字艺术怎么去探寻古代,做一些这种边缘学科的连接,我觉得可能这些也是有一些可能性的。因为只是从本系统里面找,我觉得非常困难,这还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许柏成:王老师您作为一个学者和策展人您怎么看?
王端廷:就他们刚才谈的,已经谈得非常的好了,技术是一个方面,艺术家永远面对的是人的心理、生命等一些本质性的问题。一个艺术家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一定要发现和解决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这个就来自于艺术家的他的修养、他的观念、他的敏感、甚至于他的悲悯之心。他对自己的个体生命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中所遭到的各种各样的遭遇,既出自个人,同时又带有普遍性的一些精神层面的内涵的一种发掘和揭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数字技术运用在最前卫的可能是电子游戏,但是电子游戏为什么不能作为人的一种精神产品来看待?就是因为它缺少一种深刻的内涵。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游戏都是浅薄的,但是它的职责不是在于揭示人的心灵。数字艺术致力于发掘人的心理,表现人的心理,解决人的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功能等一些问题,这是超越媒介的,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想无论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在这个方面做得好就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许柏成:张小涛老师的《量量历险记》里面,曾经有很多的场景出现马远夏圭,缪晓春老师刚刚提到白南准佛像和电视的作品,这种东方意识和数字艺术的这种结合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风格?
张小涛: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挥之不去的,它在你的血液里面,不用讲趣味、形式感或是对语言的迷恋,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感动。在几千年的文脉当中有这个线索,我觉得它是比较内在的,就像太极拳一样绵延,就是你的思维方式。所以你看像日本的物派,它同时对西方的极简,以及贫穷艺术、大地艺术有吸收,日本会出物派,和它的这种枯寂美学、东方美学和传统文脉是比较一致的。我看冯梦波这一次的作品,其实也是在修正这种过度的技术化或西方化的一些新媒体概念,我觉得只要是艺术家内心是有感受的,有自己文化的源头,就是可以的,甚至你看台湾的艺术家比我们做的更加有东方韵味。这次我在苏州的个展,名字叫做《空影》,其实来源于我做《萨迦》那个开篇的藏传佛教那个手印,那个阴影和空的东西。我觉得只要你在那个文化当中生长,它就像鸦片和毒素一样,你是摆脱不掉的。我觉得这个是越到后来越摆不掉,是这个样子的。
缪晓春:其实一开始做《虚拟最后审判》的时候,因为当时是用一个数码的模型取代了里面所有的人物,那个时候就突然感觉面对那样的一个画面,因为是同一个人,没有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之间的差别,我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他们突然变成了同一个人,同一类型的人。我最后是用佛教的众生平等来解释他们,你看这些人是一样的身份,一样的性别,最后就已经根本就没有西方宗教里面那种审判与被审判的差别,所以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接受了它,而这个完全是东方的一种哲学观,或者是宗教里面才有的一种东西,这是从内容上来说。第二个从形式上来说,08年的时候,在做三维动画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很大系列,就是《北京手卷》,《北京手卷》就是用数字来处理所有的拍摄的图片来做成像国画一样的东西。那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用笔墨纸砚,只是用软件,但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还完全是跟传统艺术当中的这种东西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说,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继承传统艺术,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跟传统产生一个联系。所以这种联系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脱不掉的一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