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年,“披头士”引领了一场流行音乐革命,从此改变了世界流行音乐的格局。

1964年初,库布里克的荒诞杰作《奇爱博士》上映。这部作品原本定于1963年上映,但由于肯尼迪遇刺事件而推迟了档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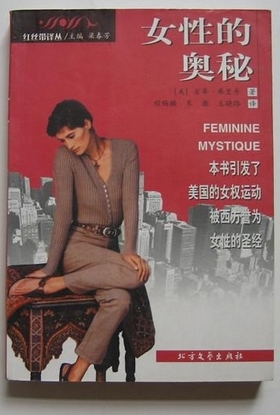
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女性的奥秘》在1963年出版。

1963年,鲍勃·迪伦出了被公认为经典的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

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1963年,出生于巴基斯坦的英国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刚满20岁,还是一名学生的他亲眼目睹了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非凡巨变。那一年定义了后来的“现代社会”。回忆起1963年,塔里克说:“那是充满预示性的一年。在当时,甚至几年后,没有人想到会发生什么,直到那场席卷全球的风暴。”他试图回想起这一年,找到内心深处的一些回忆,哪怕只有一点点印象,也可以重建一个没有太多扭曲的模糊过往。
“1963年10月,我到牛津大学读书,当时正流行波西米亚风,女人穿着黑色塑体衣或皮夹克,男人都穿皮夹克或海军防雨衣,而我固执地穿了好几个月的马裤呢和粗呢大衣。古巴导弹危机临时触发了核裁军运动,实际上英国工党会议在1960年已经投票通过了单边核裁军,但是第二年又改主意了,其中左翼工党领袖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产生了重要影响。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觉得核裁军运动太温和了,从主席位置上辞职并创立了反战团体百人会。”
女人爱披头士
男人爱滚石
1963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披头士。所有在卡法克斯交叉路口附近听过他们唱歌的人都被迷住了。在各个聚会,披头士党和滚石党整天吵闹不停,后者认为滚石无疑更优秀,更刺激,更有感觉,也更适合跳舞。“有一次我们搞了个投票,结果女人大多喜欢披头士,而男子汉都热爱滚石。”塔里克说。
鲍勃·迪伦也在人们的谈论中。他刚刚发布了那张著名的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这位“铃鼓先生”(2004年一首新歌的歌名)为无数暗送秋波和勾引提供了前戏的音乐。避孕药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女人获得更多自由,但性别歧视仍然可怕。巴黎索邦大学的新生朱迪思·奥克丽(Judith Okely)开始提倡女权主义,并把西蒙·波伏娃的作品介绍给众人。
这一年,迪伦和女朋友苏西·罗托洛搬到了乡村。她的父母是“麦卡锡主义时代”(注:19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了美国全国性反共“十字军运动”。他任职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著名人士如演员查理·卓别林和“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为向苏联透露机密和为苏联充当间谍)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他们令迪伦变得激进,使他写下了1964年那首《时代正在变化》(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这首歌推动了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注:二战后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民主权利而发起了民权运动),令那些原本对肯尼迪总统抱有很大期望的学生更加激进,他们在期望中收获的只有猪湾入侵事件和越战,同样令他们失望的还有下一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8月,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触动了整整一代人。在内战将近一个世纪后,美国黑人依然在被处以私刑,被剥夺基本人权,在南方诸州不允许投票,在北方遭到歧视。3K党在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支持者。他们决定回击,马丁·路德·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按照另两位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和马尔克姆·X(Malcolm X)的说法,不排除暴力的可能。
“纪录片”《奇爱博士》
“我记得很清楚,”塔里克说,“1963年11月22日,我和一群朋友正坐在牛津辩论社的电视机前看早间新闻。突然间,天昏地暗。我们沉默地看着电视画面,约翰·肯尼迪被刺杀了。我们谁也没说话,径直走到了酒吧。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漂亮、娇小、脸色苍白、鬈头发的朱迪思·G,她是共产党俱乐部的坚定分子。我告诉他肯尼迪被刺杀了,她面无表情地说,‘他们没有把林登·约翰逊也杀了?’她总是那样装腔作势。”
关于谁指使了刺杀行动的辩论第二天就开始了,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三个月后,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荒诞杰作《奇爱博士》上映。片中一群正在准备核屠杀的疯子控制了五角大楼,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英国喜剧演员)在其中扮演焦虑的总统大人。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Galbraith)告诉塔里克:“在我们家《奇爱博士》一直被当做纪录片。”他的父亲J.K.加尔布雷斯是肯尼迪的密友。塔里克评价:“一些将军傲慢无礼,一些只是偏执妄想。”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些领导人的地位摇摇欲坠: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都被各种各样的性丑闻或国家安全丑闻拉下了水。尽管1945年开始宣扬“社会主义精神”,但1963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绝对服从的精神主导了政治文化。新的工党领导人哈罗德·威尔逊事实上只是杰出的反对党领袖,擅长在每个方面挑战、嘲笑和抨击保守党。
“讽刺”带领社会
走向现代性
塔里克说:“实际上,真正带领社会走向现代性的是电影制片人、剧作家和讽刺作家。”电视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并非人人拥有,因此大家通常集体观看。美国数学教授汤姆·莱勒(Tom Lehrer)用他的讽刺歌拿中产阶级取乐,在基辛格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后,他开始拒绝演唱,因为“讽刺已经不可能了”。他旁边还有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舞台上最聪明和最粗鲁的喜剧演员之一,他神志不清语无伦次的意识流表演被认为破坏力太强,最终以“猥亵罪”在旧金山被逮捕,并因1962年在彼得·库克(Peter Cook,英国喜剧演员、讽刺作家)“建立”(Establishment)俱乐部的演出而被英国永久驱逐出境。
在英国,讽刺和时事评论杂志《私家侦探》已经出现,而BBC英国广播电台正在播放讽刺喜剧《上周发生了什么》(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每周有一千万观众收看。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英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作家、记者)和威利·拉什顿(Willie Rushton,英国漫画家、讽刺作家)在里面出演,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英国电视编剧),彼得·库克,理查德·英格拉姆(Richard Ingrams,记者、《私家侦探》编辑),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英国演员)等人则帮忙写段子。
塔里克说,如果要看最新的欧洲电影,要去牛津沃尔顿街的“斯卡拉”(Scala)电影院——后来是牛津街的“学院”(Academy)——和汉普斯特德的“人人”(Everyman)。“我的第一次观影经验很有教育意义。在斯卡拉放映完波兰导演安德烈·瓦伊达的《灰烬与钻石》后,他们放了《天佑女王》(英国国歌)。我几乎本能地站了起来,就像我在故乡拉合尔听到国歌时的反应一样,结果后一排的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坐下,你个法西斯!’后来我再没犯过这样的错误。”法国新浪潮富含启示,光是让-雅克·戈达尔的电影便如一颗子弹——《蔑视》、《不法之徒》、《已婚女人》、《狂人皮埃罗》、《我略知她一二》、《中国姑娘》、《周末》统治了电影界整整十年。这并不是说英国电影业已死,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这对拍档在那一年带来了《仆人》,一部描绘阶级和性压抑的强大电影,精巧的镜头令它成为时尚经典。影片展现出浓郁的同人气质,而同性恋直到1967年才合法化。此外还有约翰·施莱辛格(John Schlesinger)的《说谎者比利》、托尼·理查德森(Tony Richardson)的《汤姆·琼斯》和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的《如此运动生涯》,都是当时的先驱者。
“我在英国看的第一部戏是琼·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的《噢!多可爱的战争》,这部戏是对音乐厅文化和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感人致敬。”琼在当时解释说,“布莱希特的作品我们从1930年代就开始熟悉了。”这部戏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解构,“明年2014年100年纪念的时候应该再演一次。”塔里克说。皇家宫廷剧院是伦敦当时最活跃的剧院,既有贝克特(Beckett,爱尔兰戏剧大师)和尤尼斯库(Ionescu,荒诞派戏剧大师),又马不停蹄地上演新戏。品特(Harold Pinter,英国剧作家)的三幕戏《看管人》在这一年首演,而后来最重要的国际剧场导演之一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当时是利特伍德的忠实粉丝,正沉浸在一项挑战戏剧传统的伟大工作中。
50年后,人们不笑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文化反映出日益增长的自信。“我的一些大学朋友正在反叛一切:教授、考试、学校,还有生活本身。他们追求整个世界,寻找它只为了毁灭它,他们马上也要这样对待自己。”塔里克说。
1963年,塔里克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食物。“我到英国一周后便去了当地一家印度餐厅,名字叫泰姬陵。太可怕了!”他叫来餐厅经理问为什么这里的饭菜连流浪狗吃的都不如。经理很生气,把塔里克叫到办公室,“你刚来吗?那以后就不要来了。牛津北部有一个旁遮普妇女每周末都会烧可口的食物,你可以提前预订。”那家餐厅短期内拯救了塔里克,但他还是决定自己学烧饭,后来他从未后悔过学会这项技能。“简直无法相信30年后这个国家居然以它的饭店和美食闻名。奇迹总会发生。”
1965年,在多次食言的工党政府新一轮选举后一年,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英国前工党领袖)因为其领导哈罗德·威尔逊被指责拍美国马屁而绝望地咆哮,“你们这群白痴,难道没有意识到威尔逊是你们将会碰到的最杰出的首相吗?”充满讽刺的笑声激怒了他。但是现在人们不笑了。
50年后,全球化使欧洲的政治和文化更加趋于地方化。英国已经没有电影业可言了,甚至连肯·洛奇(Ken Loach,英国独立电影导演)也要从欧洲其他国家获得投资,欧洲电影很大程度上已经沦落到模仿好莱坞恐怖片和动作片的地步,它引以为豪的电影已经死了。它的文学眼光紧盯着《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它的作家沉迷于作品被翻译成美式英语,它的政治重复着华盛顿的节奏。最有趣的电影出自伊朗人、韩国人和泰国人之手,最有挑战的政治发生在南美,而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心已经东渡到了中国。“不要担心,”塔里克说,“北美和欧洲仍旧占据着军火工业。无人机主宰着政治和文化,或许它们也能成为军需产业的畅销冠军。”
(本文系塔里克·阿里发表在《卫报》的同名文章,早报记者据此文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