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郑闻
“蓝色总是带有阴影感,在鼎盛阶段倾向于黑暗。它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然而又作为透明的气氛出现。在地球的大气中,蓝色的出现有最明亮的天蓝色晴空,也有最深沉的蓝黑色夜空。蓝色以信仰的颤动把我们的精神召唤到无限遥远的精神境界。”
——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
茫然若失的面孔、托着面颊的手、一截扭转的躯干、一盆正在生长或正在衰败的植物……蓝色与黑色的细微颗粒在水中溶解,经过笔触的裹挟或肆意的泼洒,或深或浅地渗入纸的纹理,构成了图像的一个个基本原子。而每一幅图像,经由张月标志性的蓝色与黑色水彩的描绘,也构成了她精神世界的一个个分形。每个孤立的人类个体,只有经过充满困惑的探索和发现,才能找到一种与自身命运相处的特别方式。即便如此,这种方式也仅属于其个体本身,很难言说或与他人分享。有幸的是,我们还有语言和文字之外的方式,得以感受并触摸另一些个体丰富的内心。来自中国上海的艺术家张月,正是借助绘画,表达了她对艺术和生命丰富又敏感的领悟。如果说张月的绘画是一部部曲目,毫无例外,它们总是被这样一些旋律和氛围所萦绕:内敛、平静、些许的脆弱和忧郁、冥想、沉思,以及超脱。

张月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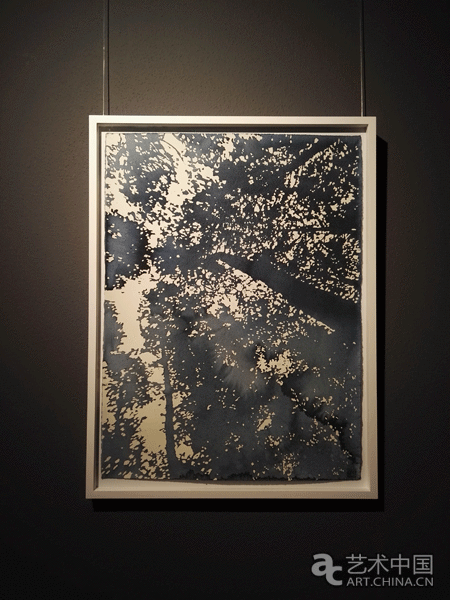
张月作品
“我觉得每个人都摆脱不了宿命,当我去读每个不同眼神的时候,在那些不同的眼神背后我都看到宿命这两个字,当我不知为何总去观察去体悟每个生命个体的时候,我的宿命也在此闪现出来……哭着的未必就是悲伤,笑着的未必就是快乐,隐忍的外表下总是渴望着精神的自由,最微弱的气息也是一种决绝。”在《默默》和《寂静》这些系列中,张月追求“去表情化”的表达,她拍摄了一些女性朋友以及自己的肖像照片,并根据这些抓拍的瞬间进行绘画创作。在所有的瞬间中,模特没有任何做作的成分——神态、表情、肢体语言,都近乎放空的状态。“我画所有东西都是一个自省的过程。”张月追求抽离一切表象以后那种她称之为接近“神性”的单纯,这种单纯对她来说反而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可能。在一个抽离所有表情、物质、时代、欲望的状态下,绘画对于她来说,才是一种接近神性的、内在的、自省的,同时也是自由的过程。
张月在绘画行动中追求生命境界,这与东方宗教关照内心的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她渴望“不用追求任何外在的事物,也不用被任何外在事物所影响”的纯粹状态。她用“寂静”这个词为人类去掉喜怒哀乐以后的精神样貌来命名。正如东方宗教中一再强调的破除执念,什么都在意的人反而什么都得不到,太过喧嚣的外物反而有损精神的纯粹。张月甚至在绘画语言和表达中,也采用了这样的理念——正如马琳·杜马斯、毛焰等画家,擅长将有限的色系运用到极致,张月非常节制地使用单色系进行绘画,却并行不悖地在单独的色系中追求非常微妙的变化——从冷暖到明暗、从纯度到色相、水份的浓淡和颜料的沉淀,以及笔触的干湿、痕迹的力量变化等等,随处可见一种单纯到极致的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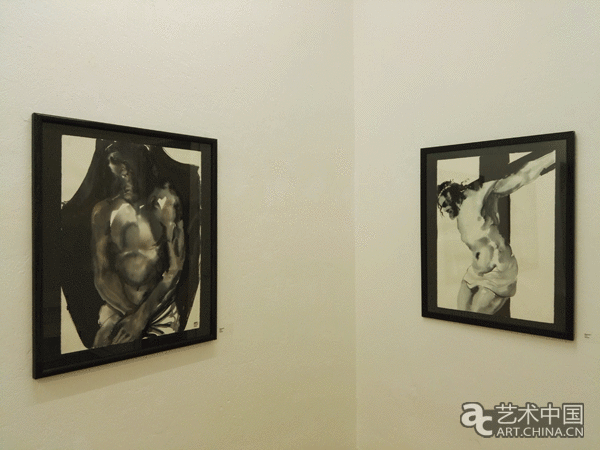
张月德国展览现场
2011年始,张月开始愈来愈多地使用蓝色。蓝色性格中的隐退与柔和,深刻的信仰,也常在《天使报喜》之类的西方古典绘画题材中看到。张月《神往》系列的创作过程兼具可控和偶发,艺术家意图抹去由笔触构成的绘画基本工序——她先谨慎地封锁轮廓,再自由感性地泼洒颜料,用另一种方式展示自然。张月把仰视视角的树木照片用幻灯投射在长一米五宽一米的大幅画纸上,用遮挡液把树木枝丫和叶子间天空的区域仔细封住,然后肆无忌惮地用水桶向画纸泼出蓝色水彩,接着加入适当的人为干预,制造出光影的深浅。画面上的天空作为留白,树木则被或深沉或轻盈的蓝色占据,留下颜色反复渲染冲刷的自然趋势,以及水迹褪去干涸的痕迹。树木与天空的界线面临着来自水和蓝色颜料充满力量的冲击,深色的部分深沉有如印蓝纸,而浅色的部分则趋于破晓前天空的灰蓝色。去掉遮挡液,水彩干透后那些水渍则形成了透明和美妙的光晕。这些蓝色在欧洲古典绘画中时常可见——圣母玛利亚在暗自侧耳倾听时,穿的是蓝色衣服。罗吉尔·凡·德·韦登( Rogier Van Der Weyden)的《主显节祭坛画》与格吕内瓦尔德(Mathis Grunewald) 的《嘲笑基督》中,基督的衣服就是类似《神往》中的那种非常独特的淡蓝色。怀着坚定的信仰,基督以消极而超脱的姿态忍受着侮辱。《伊萨汉姆祭坛画》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中,圣安东尼也穿着几乎是同样蓝色的衣服。“从有形空间的观点来看,正如红色总是积极的一样,蓝色总是消极的。然而从无形的精神观点来看,蓝色似乎是积极的,红色则是消极的。”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在著作《色彩艺术:色彩的主观经验与客观原理》中,用这样一段话标注了蓝色精神性的倾向与形而上的存在方式。
而在《界外》这个系列中,出现了更多西方宗教题材中的男性形象——如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以及鲁本斯的油画,张月用水性材料重现了它们的局部。与对女性的自省式观察不同,张月在这个系列中体现出某种隐藏的批判性视角,她捕捉了象征强健的、力量的、征服的、无所不能的男性人体,在力量丧失或者说神性抽离以后无能为力的瞬间。同时,她所使用的绘画语言也与原作存在的古典时期大相径庭,如果说古典时代的艺术家们通过不厌其烦的、外科手术般精确的解剖和细节塑造人物的形象动态和质感,张月则截取经典形象的部分躯干,以充满现代感的、高度简炼和概括的笔法勾勒出来,作为一种与她精神美学相吻合的视觉象征体。张月绘画的意义并不在描绘躯体本身,而只不过是借此强化了人在神性抽离以后无可奈何的精神状况。比如她重新描绘米开朗基罗雕塑想要努力从石头中挣脱出来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映射的是现代人类在精神力丧失以后的颓废与厌世意味,也正是信仰没落的现代人的精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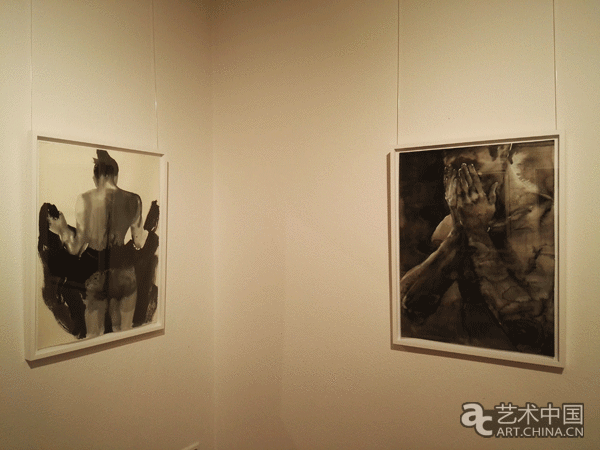
2013年我和张月合作的一个展览中,她展出了一组题为《我等待着,你却没有回答》的大型组画。这组画是《界外》系列的放大化和局部化,也是这类题材高度成熟后的一次集中展示。这批画的形象来源于她在欧洲拍摄的大量受难基督像,还有各种濒临死亡的雕塑与绘画形象。一共由十多幅竖构图的独立人体,共同组成了7米长的大幅水彩作品。其中两到三幅伸展的女人体局部作为生命的舒展,与男性的受难躯干形成了对比,使这些并置的瞬间拥有了极大的张力和悲怆的情感。这组绘画不但显示了水彩画难得一见的“强劲”风格与表现力——兼具了西方具象艺术严谨准确的造型能力、现代绘画的简练概括、水性材料的流动性与偶然性、甚至中国水墨绘画的氤氲之气——这几点的完美融合,使水彩绘画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强大气场和精神感召力,让人直击艺术家的坚韧内心。
“也许我的作品应该是形象之外,物质之外,世界之外的精神理想。”——我时常感觉,张月单色系的绘画,也可看作是她对于所绘图像,对于这个由无所不在的日常图象构成的“景观社会”或“花花世界”的一种“超度”——一如那幅闭上双目,双手按着太阳穴的男人肖像。张月偶然从日常图象的世界中截取了这幅照片,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描绘,或者说“超度”了它。类似于黑白摄影,单色系绘画屏蔽了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彩色照片和彩色现实代表的某种“窥淫癖”的不雅视角。张月的单色系绘画使观者将注意力更明确地集中到她笔端的精神性上。“赐予”作为张月慕尼黑个展的标题,也意在表达良好的祝福。对于张月来说,她的生命、艺术、才华都是来自命运的“赐予”,而对于张月作品的观众、评论者、策展人而言,我们穿过历史的重重时空,与她恰巧在同一个时代相遇,也是来自命运的巧合与美好的“赐予”。使张月深深着迷的,种种灵魂出窍或思绪抽空的瞬间状态——无论是在罗伦索·贝里尼的圣特蕾莎的脸上,还是米开朗基罗濒死的奴隶的身上,她都看到了自己,同时也忘却了自己。而那一刻,我猜她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她是微笑的。